“叨叨傅”是一位自媒体博主,其创作的内容多与“地域梗”特别是江苏的“地域梗”有关,在苏超爆火之前,其就已经创造出了有关于江苏的多个热梗,如“江苏十三太保”、“南哥”、“灌氏brothers”等,苏超爆火之后,“叨叨傅”更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在“玩梗”的路上越走越远,网友纷纷跑到他的作品下留言说:“这乱世如你所愿”,更有网友将其称为“散装江苏的始作俑者”、“江苏内斗的头号罪臣”。不过“叨叨傅”倒也是谦虚,他回应说,江苏内斗自刘邦、项羽就开始了。言外之意,他的“梗”不过是“再现”了某种现实,而非“建构”现实。但是“梗”的力量真的只能是“再现”而无法“建构”么?事实上,“梗”与现实的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加深刻地“纠缠”着。

2025年6月15日,江苏无锡,2025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4轮,无锡队Vs常州队。“长三角段子手”叨叨傅现身观众席。
“梗”,这个词,你似乎很难说出其是何时进入大众的言谈之中,甚至难以用一个确切的定义来告诉别人是什么。实际上,当我们试图去定义某物的时候,已经将事物为何交给了语言,所以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就是:“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本文并不纠结于如何定义“梗”,甚至这也不重要,而是想指出,如果从修辞传播学来理解的话,“梗”更像是一种“幻想”(fantasy)的结晶。“幻想”这个词是美国传播学者鲍曼(Ernest G. Bormann)等人所提出的一个术语,在这里,“幻想”并不是那种脱离于现实的虚构,而是人们出于心理或者修辞的需要,对事件进行的富有想象性(imaginative)和创造性(creative)的一种诠释,[1]人类的这种“幻想”天性对于其在社会这一象征环境或者修辞环境中存活下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里,不必狭隘地将修辞理解为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实际上,修辞一词在西方的社会语境中,其含义甚广。在西方的古典修辞学中,修辞学研究的是人如何运用演讲来规劝或说服听众,而当代的西方修辞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运用包括语言运用在内的符号手段去影响他者的观念和行为,[2]如果我们将“修辞这一概念界定在运用话语和象征来达到某种目的的话,那么,其对象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文化现象。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环境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象征环境,也就是一个修辞环境。我们不仅解读修辞文本,而且制造修辞文本。
人生来就有“修辞”的动机,有着用语言编织“幻想”的天性。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就认为,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不是建立在逻辑的思维方式之上的,而是有着其独特的“神话思维”方式,这也是他所谓的“隐喻思维”(metaphorical thinking)概念。他的《语言与神话》一书即是想说明,这种神话的隐喻思维实际上乃是人类最原初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而“语言”这一人类思维的“器官”就其本质而言首先也是“隐喻的”而非逻辑的。[3]卡西尔的这一思想用朗格(Susanne K. Langer)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作为人类首要的推理工具的语言,其实现的更多是一种创造神话的倾向,而不是理性化的倾向。[4]
鲍曼认为,“面对重大事件的千头万绪和似乎是不可改变的社会或自然压力,个人往往感到茫然无助”,而应对这种情形的一个方法就是进行“幻想”,以帮助自己去理解和适应[5]。换而言之,人类生来即是一种会“幻想”的动物,会对外部世界进行一种戏剧化的想象,或者,通俗来说,人们总是愿意以一种语言编排的方式,对外部世界加以理解和诠释,最终达到一种心理上的舒适。即使是那些确定性的事件,人们还是会根据自己特有的“幻想”对这些事情进行诠释。如在足球比赛中,获得点球的一方,往往会认为获得点球是队员拼搏之后,“天道酬勤”的奖励,而被判罚的一方,往往会将对方形容为“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而当事情本身就是“不清不楚”的时候,这样反而更加会激发人们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各种有利于我的诠释,[6]如当一个刑事案件发生时,警方还未公布案件详情,关于案件的各种推测和想象就已经流传于网络中了,但无一例外,这些想象都是基于某种戏剧化的安排,案件当中的人被安排了各种各样的角色,如“厌世者”、“反社会人格者”、“受压抑者”、“被压迫者”,在这种角色安排之下,案件当中的人的行为便有了一些合理化的诠释。
鲍曼指出,一些历史进程也都可以用“幻想”驱动来解释,如鲍曼认为,北美大陆的早期开拓者便共享了如下“幻想”:他们将向北美新大陆的移民视为是“被上帝选中的子民”的神圣迁徙,就如同是圣经故事中所说的犹太人从埃及前往迦南一样荣耀。在这种“幻想”之下,清教徒们将征服新大陆视为是为上帝开疆拓土和拯救北美土著的灵魂的过程,而征服过程中出现的干旱气候或者印第安人的突袭等开疆拓土中的困难,在清教徒们看来则是上帝不满的证据,是上帝在惩罚他们,因此他们应当做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去取悦上帝。[7]
换而言之,人在社会这一象征或者修辞环境中,需要进行“幻想”以解释社会的运行,而人一旦执迷于某种“幻想”,所有那些正常或者荒谬的事情都得到了合理化的解释,这就是“幻想”的力量。鲍曼在1985年出版了《幻想的力量:重新恢复美国梦》(The Force of Fantasy: Restoring the American Dream)一书,以美国梦这一“幻想主题”诠释了1620年至1860年间的美国历史。在鲍曼看来,正是因为美国梦对于共识的凝聚,才使得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成为可能。
鲍曼等人也据此发展出了一个一般性的传播理论符号融合理论(symbolic convergence theory),也有学者将其翻译为象征趋同理论,但无论何种译法,实际上都在强调个体与个体的“幻想”达到融合或者趋于一致。因而符号融合理论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就是:“一是社会现实是在交际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是用符号建构起来的,或者更具体说是用“幻想”构建的;二是人们在交际中有一种想象性地向彼此靠拢的倾向。”[8]
第一个假设实际上指出了符号的建构性力量。语言或者修辞行为在构建我们的社会环境。美国著名修辞学者伯克(Kennteh Burke)指出,“术语不仅影响我们观察的内容,而且我们的许多观察就是因为这些术语产生的,因而,我们当作‘现实’的种种观察,不过是这些术语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可能性’而已”。[9]而“幻想”作为一种对于现实的抽象理解,也是存在于修辞之中,“幻想”构建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修辞行为。
鲍曼指出,一些传播学者认为“意义在于人而非信息”这一说法未免太过简单,在很大程度上,意义就是存在于信息之中[10]。中国台湾地区传播学者林静伶曾研究过台湾一家“多层次传销公司”如何经由语言符号而建立“幻想”的共享的,她摘录的传销公司刊物的一句话如下:“能将传统事业做得好的人,是不平凡的,因为他用了不平凡的方法与努力,去成就平凡的事业;但在传销的世界里,没有学历、男女老幼的分别,只要是平凡人,用平凡的方法与努力,就可以成就不平凡的事业。”[11]对于那些寻求出路寻求认可的社会底层来说,这段话无疑是有号召力的。因而,鲍曼等人指出,群体的“幻想”到最后也是一种修辞视野(rhetorical vision),“之所以选择用‘修辞’这一术语,是因为修辞的想象语言引发了幻想共享,并导致了更宏大的符号结构的产生”。[12]
而这个理论的第二个假设阐明了一种群体的动力学机制,即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幻想”是可以融合的。美国传播学者费舍尔(Walter R. Fisher)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说书人”(storyteller),而我们所认识的、赖以生存的整个世界即是由一连串的故事架构而成,我们听别人讲故事,同时也讲故事给别人听。[13]换而言之,“人们具有分享戏剧化叙事的趋向,这个趋向导致了劝说的潜势”[14],因而也就能够吸纳更多的人进入某种特定的叙事之中。
鲍曼也指出,人的这种叙事本性导致了“幻想”的共享,最后则是建立了群体共识和建构了某种社会真实。[15]那么所谓的“符号融合”,也就是“在交流互动中,人们会把各自的‘幻想’带入其中,随着互动的推进,人们之间的‘幻想主题’会发生链接,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幻想主题’会‘牵引’出另一个人的相似或相同的‘幻想主题’,这样,交流者之间会逐步‘戏剧化’地靠拢,达到一个共同的象征世界。”[16]如在一个小团体中,当有人提及某个人物或者事件时,他都无须讲述个中细节,团体人员就会沉默不语或者哈哈大笑起来,这就是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符号融合”。在现实生活中,你在上海人群体间说一句“苏北人”,怕大家也是会会心一笑。因为“苏北人”作为一种“幻想主题”,早已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中。
鲍曼认为,这种“符号融合”现在不仅仅发生在小群体中间,也可以发生在更大规模的公众中间。从扩散的动力机制实际上也就是传播过程来说,首先,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们聚在一起讨论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或者问题,有成员将群体所关心的主题戏剧化,这个戏剧化的主题便在群体内部产生了“复诵”(chain out)效应,因为它拨动了一个共同的心理学动力的“和弦”,或者让某个之前大家都心照不宣的议题浮出水面,或者是让他们面临的自然环境、社会政治体系或经济结构的共同难题得以公开化。群体成员开始变得兴奋和投入其中,更多的戏剧化的“复诵”创造了一个有英雄和有反派的符号真实。实际上,到这一阶段,在这个群体内部已经完成了一种共同的“幻想”叙事。当然现实生活中,很多“幻想”的实现是直接面向公众的,而不是通过小群体的这种由内而外的扩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所喊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是直接面向公众的,这句竞选口号本身业已暗藏着一种关于美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幻想”。

2025年8月2日,江苏南京,南京新街口商圈的电子大屏上,为即将开赛的“苏超”南京对盐城比赛助力。
回到苏超,赛场内,各个城市球队拼得你死我活,赛场外,各种“幻想”对这种现实加以戏剧化地编排,地方有关单位、文旅账号、官方媒体(如江苏卫视)、自媒体等竞相造“梗”,每一场比赛都是一出甚至好几出的“戏剧”。“梗”让人欢乐的地方就在于此,因为“梗”像是一种“快捷方式”,它所链接的是人们脑中编排好的戏剧。徐州和宿迁的比赛,是“2000多年前楚汉相争的延续”(注:刘邦徐州人,项羽宿迁人),而徐州人和宿迁人此刻就是这两位英雄的化身,还有什么比当一夜或者一周乃至一个夏天甚至是更长时间的刘邦和项羽更让人快乐的事情呢?当宿迁2:0领先连云港,但最后又被扳平之后,哪个连云港人又不觉得自己不是韧性十足的孙大圣的化身呢(《西游记》的花果山的原型一般被认为是现在连云港的花果山)?而宿迁又免不了被揶揄是习惯了“半场开香槟”,影射的是痛失好局的楚霸王项羽。扬州和泰州的比赛,又被“幻想”为一场“父子局”,毕竟现实是1996年,扬泰分家,从扬州分出去的泰州上升为地级市,如今苏超场上再相见,泰州何尝不想证明自己已不是当年的小阿泰,扬州又何尝不想证明,你至少应该叫我一声扬叔吧。而分走苏超一半的流量的常州队,名号从“常州霸王龙”到“吊州大蜥蜴”再到“巾州小壁虎”再到“丨州草履虫”,人们对于常州的“梗”一次又一次地精准拿捏了常州的现实,并且又留下了“悲情小人物”的“幻想”,常州队的教练雨夜一跪,更是将这出“悲情”之戏推向了高潮。
或许,有读者看到上述的“梗”也会嘴角上扬,会心一笑。不用怀疑,那是因为我们的“幻想”在此刻达到了融合。我们都爱“幻想”,并且也乐于接受和传播别人更欢乐的“幻想”,因为我们从心底里需要,在“幻想”之中,现实被解释,被我们所接受。创造“幻想”、传播“幻想”,这也是我们活在一个“神话世界”、“修辞世界”中的法则。
再回到叨叨傅所说,江苏内斗自刘邦、项羽就开始了,意谓“梗”仅仅是“再现”,但真的如此么?我们再以“苏北人”这一个“梗”为例,先有“苏北人”到上海,然后才有“苏北人”的说法。但是,当“苏北人”成为一种说法得以确立时,关于“苏北人”的“幻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凝结成形了,这种“幻想”可能包含种种戏码,但无论如何,一旦这种“幻想”凝结成形,现实是否真的如此已无人追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幻想”反而重新建构着现实,即使历经百年,这种建构力依然稳固地存在。这就是“幻想”与现实的辩证法。与苏超有关的“梗”亦然。“梗”自然是由现实所生产,没有城市GDP全部是中国百强的现实,就难以有“江苏十三太保”的“梗”,但是“梗”中包含着“幻想”,“幻想”让某种现实得以凝固,成为一种“客观化”的存在。现实并不会如“那般”地存在着,因为何为“那般”,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而是由“幻想”所建构的。换言之,一开始并不存在着一个“确定”的江苏形象,它总是被各种“幻想”所建构,但一旦变成某些热“梗”凝结下来,江苏就不再是那个江苏,而就是“散装”、“内斗”的。而之所以这些“梗”能够流传下来,是因为这些“梗”符合了大多数人对于江苏的“幻想”。人总是“幻想”的动物。
注释:
[1] Ernest G. Bormann, The symbolic convergenc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teachers and consultant,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1982, 68(3), 288-305
[2] 大卫·宁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M].常昌富、顾宝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2.
[3] 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12-13.
[4] Ernest Cassirer, Language and Myth, trans. Susanne K. Langer, New York: Harper, 1946, pp. viii-ix
[5] Ernest G. Bormann, Fantasy and rhetorical vision: The rhetorical criticism of social re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1972, 58 (4), 396-407
[6] Ernest G. Bormann, Fantasy and rhetorical vision: The rhetorical criticism of social re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1972, 58 (4), 396-407
[7] Ernest G. Bormann, Fantasy and rhetorical vision: The rhetorical criticism of social re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1972, 58 (4), 396-407
[8] 邓志勇、王懋康.幻想主题修辞批评:理论与操作[J].外语教学,2013(2):11-16.
[9] 大卫·宁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M].常昌富、顾宝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9.
[10] Ernest G. Bormann, Fantasy and rhetorical vision: The rhetorical criticism of social re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1972, 58 (4), 396-407
[11] 林静伶.语艺批评:理论与实践[M].台北:五南出版社,2000:79.
[12] Ernest G. Bormann, John F. Cragan & Donald C. Shields, Three Decades of Developing, Grounding, and Using Symbolic Convergence Theory (SCT),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01, 25 (1), 271-313
[13] Walter R. Fisher, Narration as a human communication paradigm: The case of public moral argument, Communications Monographs, 1984,51 (1), 1-22
[14] 邓志勇、王懋康.幻想主题修辞批评:理论与操作[J].外语教学,2013(2):11-16.
[15] Ernest G. Bormann, Symbolic Convergence Theory: A Communication Formul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85, 35 (4), 128-138.
[16] 邓志勇、王懋康.幻想主题修辞批评:理论与操作[J].外语教学,2013(2):1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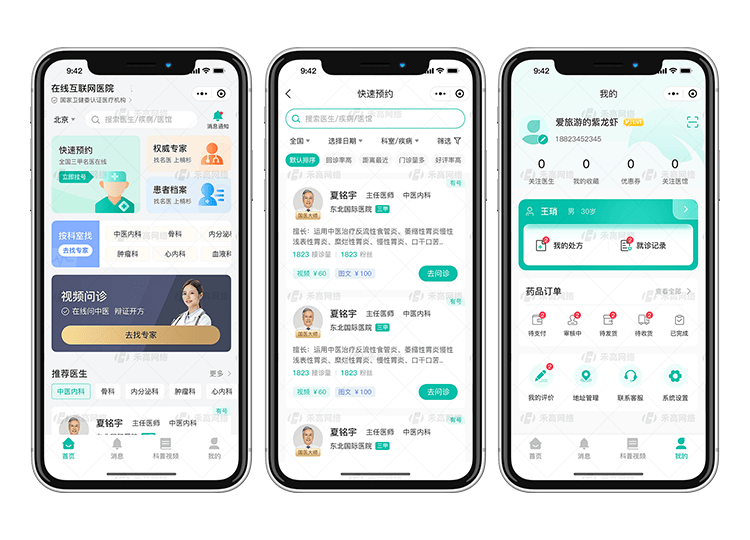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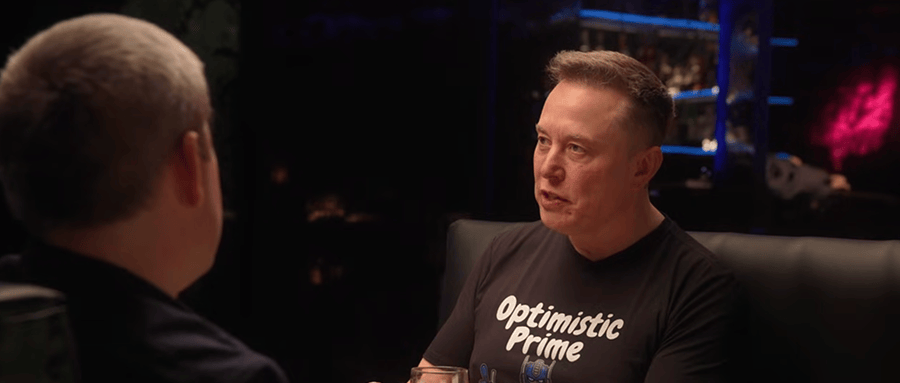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