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在互联网行业引发巨大震动。

报道指出,本应补贴给服务商和运营商的1.4亿元奖励金,被北京海淀区一家短视频平台公司的内部人员联合外部供应商非法侵吞,并通过比特币等方式完成洗白。
案件曝光后,外界一度将这起商业腐败案件的主犯冯某与前快手磁力引擎副总裁冯超联系在一起。
但据《财经故事荟》昨日独家披露,真正的涉案人是快手前电商服务商运营中心总经理冯典,他曾供职于滴滴和宝洁。
领英资料显示,冯典本硕就读于北京邮电大学,2013年硕士毕业后进入宝洁,曾负责口腔护理品类全国分销商渠道生意。

2018年12月,他跳槽至滴滴,从事运营工作,一年半后又转入快手,主要负责电商服务商管理及政策制定和落地。
2020年至2021年间,他利用手中权力设计漏洞、泄露数据,伙同外部商户套取公司补贴资金达1.4亿元,创下互联网大厂贪腐新纪录。
最终,冯典及同案另外6人因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至有期徒刑三年不等,并退缴缴92枚比特币。
金额之大,不仅令业界震惊,也让互联网大厂反腐再度成为公众热议话题。
01
权力闭环
冯典案揭示了互联网公司内部管理的一个薄弱环节:权力闭环。
冯典在快手虽非公司顶层高管,却掌握着服务商入驻审批、奖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核心权力。
正是这种看似边缘、实则关键的岗位,为其侵吞巨额资金提供了空间。
案件显示,冯典先在补贴政策中“预留”漏洞,再将本应严格保密的内部运营数据泄露给关系密切的外部供应商。
供应商们利用这些信息量身定制申请材料,从而虚构条件,套取本应属于其他商家的奖励金。
随后,冯典等人通过注册空壳公司,层层转移资金,再借助境外虚拟货币平台混淆交易路径,资金被清洗。
虽然最终东窗事发,且涉事人员于2024年9月被法院判刑,但案件暴露出的问题远超个人贪腐本身。
而冯典案并非孤例。今年以来,多起大厂贪腐案相继曝光。
7月24日,上海警方披露一起沪上某互联网企业高管收受商业贿赂案。
据悉,涉事高管为饿了么前CEO韩鎏,6月底被警方带走时为饿了么物流负责人。

2025年6月19日,一涉案人员配合上海警方调查。
警方披露,韩鎏利用物流配送业务的管理权,两年内与同僚合谋收受供应商行贿4000余万元。
7月初,B站内部邮件通报,原游戏合作部总经理张再敏因严重职务犯罪被捕。
几乎同期,完美世界通报,自查发现旗下多个工作室核心人员在职期间违规操作,部分人员因涉嫌违法犯罪被警方调查。
6月底,唯品会披露,副总裁冯佳路因涉嫌个人经济问题正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在一波接一波的曝光中,行业贪腐的共同链条逐渐清晰:资源倾斜、数据操控、流量分配、供应商准入,都可能成为贪腐的土壤。
02
贪腐画像
今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与法院发布的白皮书,对互联网腐败特征作出系统总结。
2020年至2024年间,海淀法院共审理127件涉及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的贪腐犯罪案件,涉案金额约3.05亿元,个案犯罪金额最高达6700余万元。
涉案人员中,91.13%案发时年龄在18至45岁之间;62.20%的被告人属于部门经理、总监等中层及以上岗位。
整体来看,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呈人员年轻化、职级中层化的特点。
更值得注意的是,软权力寻租日益突出。所谓软权力,并非直接掌握合同签署或资金拨付,而是平台规则中的细小操作空间,例如账号解封、推荐位调整、流量倾斜。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权限,在流量经济的驱动下,往往能换来真金白银。
软权力的存在,让商业腐败不再局限于企业中层和高管,而是延伸至了基层岗位,例如:
— 有普通运营人员,收受主播300万元以违规提供快速解封、加“白名单”等帮助;
— 有公司前台秘书,利用支付结算漏洞“蚂蚁搬家”式侵占公司钱款300余万元;
— 有平台热搜小编,收钱将话题推上热搜榜,每条收取好处费1000至2000元不等;
与此同时,贪腐团伙化趋势也日渐明显:供应商愿意重金围猎,内部员工则充当牵线人,共同分食利益。
03
公开与保密
面对频发的贪腐案件,各大互联网企业应对方式不同。
腾讯、京东、抖音等企业近年来定期对外公布反腐案例。一方面在内部起到警示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向外部合作方表明态度。
京东在2024年查处了221起贪腐案,其中包括商业贿赂191起,职务侵占30起,并将其写入年度ESG报告。
抖音则在反舞弊通报中明确披露涉事金额与处罚结果。3月底,抖音发布通报,称2024年全年共有39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相对而言,快手在冯典案中选择低调处理,据说内部要求“保密”。
业内人士分析,快手当时既处于资本市场敏感期,又在快速扩张电商业务,选择低调,既是为了避免股价进一步波动,也为稳定外部合作伙伴信心。
这种差异,折射出互联网大厂在反腐与资本市场、业务扩张之间的微妙平衡。
04
深层危机
事实上,互联网公司并非不重视反腐。近年来,随着行业进入降本增效周期,风控与内审体系正在不断强化。
然而,腐败案件依旧层出不穷。一名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内部监察总监曾在5月份的一次活动上表示:“我们互联网(企业)的工作人员可能并不比这些落马的厅局级干部贪得少。”
与国企、机关腐败的罪名体系有所不同,互联网企业贪腐通常涉及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等。
但无论怎么讲,本质问题都在于权力缺乏制衡。
互联网行业的特殊性在于,它掌握的是海量用户、流量与数据。这些新型资源,本质上已成为商业价值的硬通货。
当内部管理不完善,平台软权力容易被滥用,便催生了所谓流量腐败。
主播为快速解封付钱、商家为推荐位行贿、供应商为合同资格送礼,都是流量腐败的表现。
这类腐败不仅损害公司利益,更破坏平台生态公平。一旦外部合作方认为平台规则不透明、内部存在寻租,长期合作的基础将受到动摇。
因此,在资本与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大厂必须持续反腐,不断完善风控体系,才能避免资金的“跑冒滴漏”演变为撕裂企业根基的深层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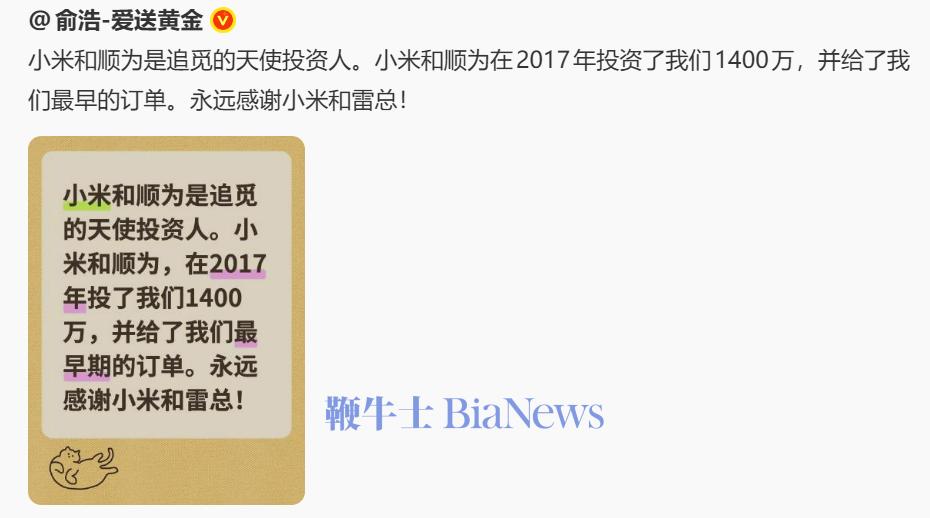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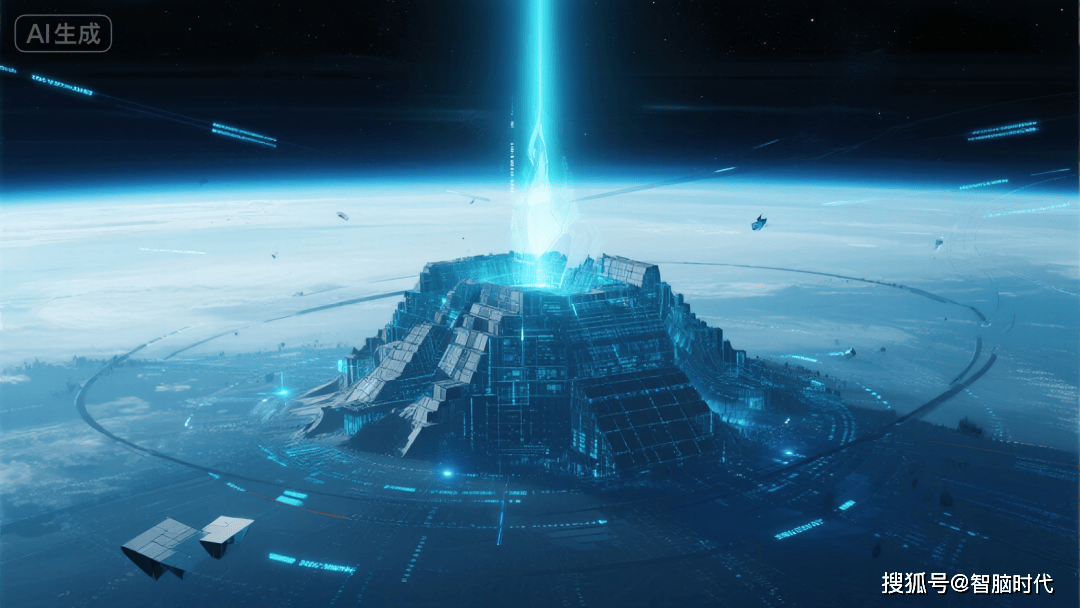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