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9月2日,Yann LeCun在他的领英页面上发布了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其指向性非常明确。
他写道:“嘿,AI领域的记者和专家们。并非每个从事AI工作的人都是‘研究员’。” 他接着定义了他心目中研究员的标准:他们倾向于公开发表至少一部分研究成果,并开源一部分代码;他们通过论文和开源代码对其他研究者和技术社区产生影响,这可以从谷歌学术的引用数和H指数上看出来;他们通常拥有一个与AI相关领域的博士学位;他们在研究生期间就发表论文,并在参加工作后继续发表。如果他们停止了发表,他们就变成了工程师或者管理者。
LeCun继续写道:“正如我之前帖子中指出的,研究和工程/产品开发是两种不同的活动,有着不同的动机、不同的激励机制和不同的操作模式。有些人两者都能做,有些人只能做其一。相当多的人在职业生涯中从研究转向工程或管理(反向的情况比较少见)。但简单来说,研究员的衡量标准是他们的智力影响,工程师的衡量标准是他们的产品影响。两者对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都是必需的。”

这段话虽然有点绕,但是不难看出Yann LeCun在暗讽,智力水平高的才能当研究者,智力水平低的是管理者,而且作为AI行业的研究者,还要具备一个博士学位。杨立昆那番意有所指的话,可能是缘于一次当面冲突。
早些时候,meta AI的首席科学家Yann LeCun正在发言,他对一项激进的人工智能开发计划表达了系统性的反对意见。LeCun是图灵奖得主,他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资历深厚,尤其是在深度学习和卷积神经网络方面的贡献,是行业公认的奠基人之一。他习惯于从基础科学的严谨性出发,审视技术发展的路径。然而,他的发言被中途打断。
打断他的人是Alexander Wang,时年28岁,是LeCun的上级。Wang直接说:“我们是在开发超级智能,不是在辩论哲学。”这句话让会议室的空气瞬间凝固。参会者们感到尴尬,LeCun本人也陷入了沉默。
这次直接的冲突,将meta AI实验室内部两种工作方式和思想的矛盾公开化。一方面是LeCun所代表的,基于长期主义和基础研究的科学探索精神;另一方面是Wang所代表的,追求速度、执行力和短期成果的工程导向文化。这个事件并非孤立的个人摩擦,它预示着一个投入巨额资金和顶尖人才的科技巨头,可能因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而在关键竞赛中步履蹒跚。
01
Yann LeCun的学术生涯始于法国,他在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学完成了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重点是机器学习,特别是神经网络。1980年代末,他在多伦多大学跟随Geoffrey Hinton进行博士后研究,之后加入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贝尔实验室。
在贝尔实验室期间,LeCun开发了卷积神经网络(CNN),这项技术通过模拟生物的视觉皮层,极大地提升了机器在图像识别领域的准确性。他将这项技术应用于手写数字识别,并成功开发出被多家银行采用的支票读取系统。CNN后来成为计算机视觉领域的标准架构,为自动驾驶、医疗影像分析、人脸识别等众多应用奠定了基础。
离开贝尔实验室后,LeCun进入学术界,成为纽约大学的教授。他在纽约大学创立了数据科学中心,继续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研究。他的工作方式始终围绕着公开发表研究成果和开源代码,以促进整个学术界的共同进步。他的谷歌学术页面记录了数百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超过数十万次,H指数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这些数据都反映了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2018年,因为在深度学习领域的开创性工作,Yann LeCun与Geoffrey Hinton、Yoshua Bengio共同获得了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图灵奖。对于LeCun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项严肃的科学事业,需要对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和持续探索,而不是简单的工程堆砌。
2013年,他加入Facebook(后来的meta),担任首席AI科学家,负责领导公司的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FAIR)。他的角色定位一直是思想领袖和顶尖科学家,负责为公司的长远技术布局提供方向,而不是一个负责具体产品交付和短期业绩指标的管理者。
Alexander Wang的职业轨迹则完全不同。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MIT)主修计算机科学和物理学,但在大一结束后就选择了辍学。这种行为在硅谷的创业文化中常常被看作是一种特质,代表着对传统路径的挑战和对商业机会的敏锐嗅觉。辍学后,Wang曾短暂在问答网站Quora担任技术主管,之后在2016年,年仅19岁的他联合创立了Scale AI公司。
Scale AI的商业模式非常直接。随着人工智能行业对高质量标注数据的需求激增,Scale AI提供了一项核心服务:数据标注。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招募大量的合同工,这些人负责对图像、文本、音频等原始数据进行分类、标记和注释,例如在自动驾驶的图像中标注出行人、车辆和交通标志。这些经过处理的数据随后被提供给谷歌、通用汽车、OpenAI等公司,用于训练他们的机器学习模型。
Scale AI的业务本质上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数据加工厂,它通过规模化和流程化的管理,将廉价的人力资源转化为AI公司所需要的数据原料。尽管其业务核心是人力,但Scale AI成功地将自己包装成一家高科技人工智能公司,并获得了资本市场的高度认可,估值一度达到数十亿美元。

Wang的成功展示了他作为一名企业家的能力,他擅长识别市场需求,并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组织资源来满足这种需求。他的方法论是实用主义和结果导向的,对于那些不能直接转化为商业成果的理论探讨,他缺乏耐心。
在ChatGPT于2022年底发布并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技术竞赛后,meta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焦虑。公司内部的战略重心开始发生偏移,从过去强调长远的基础研究,转向了不计成本地追赶竞争对手。在这样的背景下,拥有快速产品交付经验和强大执行力的管理者变得至关重要。Alexander Wang的行事风格正好契合了meta当时的迫切需求,这为他进入meta并担任高层职位铺平了道路。
于是,meta AI的组织架构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权力结构:图灵奖得主,AI界的泰斗Yann LeCun需要向比他年轻三十多岁,本科肄业的Alexander Wang汇报工作。
02
从好的一方面来说,安排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文化信号,它清晰地表明,在当时的meta,速度和执行力被放置在了经验和学术权威之上。在Wang的管理下,团队的资源和方向开始向着如何尽快推出一个能够与竞争对手抗衡的大模型产品集中。
然而,这种文化转变很快就带来了负面影响。公司内部的矛盾不仅存在于LeCun和Wang之间,也开始在团队的其他层面蔓延。Shengjia Zhao(赵胜佳)的案例就是一个证明。Zhao是meta从OpenAI高薪挖来的研究科学家,他是ChatGPT开发过程中的关键成员之一。
来到meta后,Zhao在工作中遇到了挫折。他认为自己领导的项目没有得到承诺的GPU计算资源,并且对公司的奖金分配机制感到不满。在一系列沟通未果后,Zhao向管理层发出了最后通牒,表示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他将考虑返回OpenAI。

Zhao的遭遇反映了meta AI内部更广泛的问题。“雇佣兵”文化开始盛行,公司用高薪吸引顶尖人才,但却没有提供一个能够让他们安心工作的环境。这些高薪挖来的人才发现,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争夺有限的资源,并应对复杂的内部政治。协同创新的氛围被内耗所取代。
那些拿着高薪的顶尖人才感到自己的专业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发挥,而团队里的普通工程师和研究员则因为感到资源分配不公和缺乏明确的发展路径而普遍士气低落。最终,为了控制成本和应对内部的混乱局面,meta在一段时间后暂停了部分团队的人才招聘,这标志着前期“大跃进”式扩张的失败,公司被迫进入一个收缩和调整的阶段。
03
产品层面,在Wang到来之前,meta AI就已经有些不对劲了。meta的Llama系列大语言模型最初在开源社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Llama 2的发布,其性能在当时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开源模型,并且在许多基准测试中表现出与一些闭源商业模型相近的能力。Llama 2的成功,让meta在开源AI领域获得了声誉,被看作是能够与OpenAI和谷歌抗衡的重要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FAIR实验室长期以来的技术积累。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Llama 4的时候,市场上开始出现对其性能指标的质疑。一些第三方评测机构和社区开发者发现,Llama 4在某些公开基准测试中得分很高,但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其真实能力似乎未能达到宣传的水平。有传闻指出,该模型可能在训练过程中针对特定的评测基准进行了过度优化,以求在排行榜上获得一个好看的数字。这种做法被批评为一种“应试教育”式的开发,甚至是一种数据造假。

从Llama 2作为最强开源模型的引领者,到Llama 4发布时面临被Grok、Claude等后起之秀超越的境地,并且声誉受损,这背后是战略上的失败。meta投入了千亿级别的资金,吸纳了全球最优秀的一批人工智能人才,最终却发现在最核心的大模型主赛道上,自己从一个有力的竞争者,逐渐变成了一个追赶者,甚至有掉队的风险。
从Llama 4的作弊刷分,再到现如今的“雇佣兵”团队,meta正在表达着一种“唯结果论”的味道。当一个团队的文化导向变成了不计代价地达成某个短期目标时,产品的长期可靠性和真实能力就可能被牺牲。
meta AI内部的氛围最终对创新本身造成了抑制。一个不尊重专业知识、急功近利、充满内部斗争的文化环境,直接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像LeCun这样的科学家和像Zhao这样的关键工程师,都无法在一个内耗严重的环境中长期高效地工作。而决策的短视化,还可能会将这个问题进一步放大。管理层为了追求短期的产品发布和性能指标,忽视了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和技术的长期健康发展。
其结果也显而易见,仓促的产品开发流程导致了模型的缺陷和性能的不稳定。
在人工智能这样一个需要深度创新、持续投入和长远眼光的领域,团队的文化和使命感至关重要。一个由共同使命感和相互信任驱动的团队,其长期战斗力远超过一个仅仅依靠高薪和短期目标驱动的“雇佣兵”团队。OpenAI的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曾经对此发表过评论,他的话在后来被证明具有预见性。他说:“在我看来,meta正在做的事情将导致非常严重的文化问题......有使命的人终将击败雇佣兵。”
Yann LeCun与Alexander Wang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meta AI的一系列问题,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内部管理失误。它反映了在当前这轮AI浪潮中,硅谷乃至整个科技行业所面临的一种根本性的价值观冲突:代表严谨科学精神和长远探索的“传教士”文化,与代表商业效率和短期回报的“雇佣兵”文化之间的对决。
meta AI的遭遇,为所有试图在人工智能时代取得成功的公司提供了一个案例: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能够激励真正创新的内部文化,再多的资金和人才,最终可能也只是建造了一座看似华丽,但地基不稳的空中楼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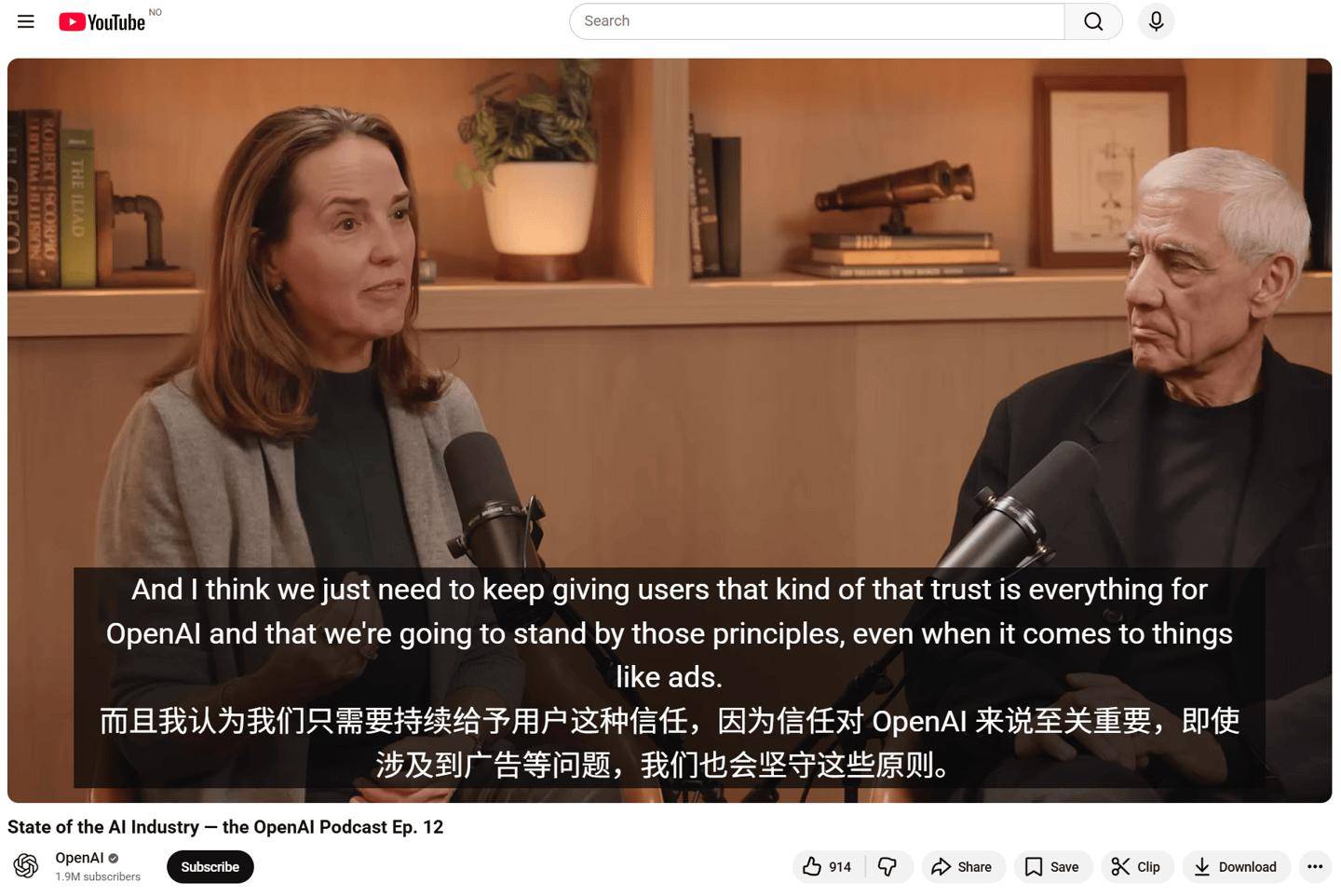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