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近期,上海市启动“十五五”规划“百家访谈、万家调研”活动,广泛征集社会各界对“十五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建议。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共同开展对战略科学家、决策咨询专家的深度访谈,受访专家作为各自领域的顶尖人才,既有对相关行业的一线观察,更有面向未来的战略思考,共同助力上海“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
本期受访专家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海波。

陈海波教授在办公。徐瑞哲 摄
陈海波,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ACM(国际计算机协会)、CCF(中国计算机学会)、IEEE(国际电子与电气工程师协会)会士(Fellow),开源鸿蒙项目群技术指导委员会创始主席,也是国际计算机协会操作系统专委会(ACM SIGOPS)自1965年成立以来首位来自非北美的主席。
长期从事操作系统、分布式系统等基础软件的研究、产业与生态工作。按照csrankings.org统计,其近十年在操作系统领域顶会(SOSP/OSDI)上发表的论文数居世界第一。研究成果通过产学研深度结合被应用到数十亿设备,为我国操作系统研究与产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产生了广泛的学术与产业影响。

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一角。徐瑞哲 摄
本报记者 徐瑞哲
记者: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人工智能时代的“入口”,作为长期深耕科技领域的学者,您觉得支撑AI时代运行的庞大基础架构具体指什么?很多人会联想到英伟达的CUDA生态链,也有声音提到信创平台,您如何看待这些不同技术路径的关系?
陈海波: AI时代,我们的基础软硬件体系,必须也必然会走向自主可控。如果一直依赖“卡脖子”的生态链条,我们的AI发展就会受制于人。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和生态格局也已初步形成,包括开源鸿蒙等。我相信,以我国的技术积累和市场体量,完全可以凝心聚力,主导从底层开始的技术攻关,开放性地打造出一到两套完整、好用易用的生态体系,实现“换道超车”与自主发展。
AI生态的建设需要体系化,各类数据资源的整合、各类应用场景,以及社会高度关注的算力资源等等,都是生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让算力设施更好地发挥出价值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需要研究如何提高算力中心的利用率,如何让资源分布更均衡,如何通过算力云化与端云协同,来实现资源共享并降低使用门槛,等等。总之,我们需要体系化的建设,激活整个生态链条的活力。
记者: 您刚才提到AI时代的基础架构需要自主可控,而操作系统作为连接硬件和软件的“桥梁”,这种跨平台的“生态”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陈海波:生态需要互联互通,才更有生命力。开源鸿蒙的目标之一就是打通各类消费终端和行业终端,让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汽车、智能机器人,以及各行业的智能终端等,相互之间都可以“讲普通话”。而且,操作方式也不止于机器语言,还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手势、眼神等更自然的交互方式。与AI结合形成智能体,乃至面向物理世界,打造具身智能,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留给我们巨大的想象与创新空间。

练秋湖彩虹桥。徐瑞哲 摄
记者:在上海,无论是高校实验室还是创新企业,总能看到许多年轻人的身影。您作为高校教授,如何感触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是“年轻人的事业”?这种年轻化特征对行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陈海波:我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学院以及双聘的人工智能学院,“老中青”三代的确是在“接力跑”,人才有机协同。尤其是新建的人工智能学院,教职团队平均年龄仅35岁。还有更多的“少年”,也就是大学生,非常有冲劲,确实让人感慨“后生可畏”。
当然,不能“卷”人才。青年人才在发展过程中会面临各种压力,但不能因此就过度焦虑。制度设计应该有利于他们专心科研、长期探索,让青年人有能力,更要有动力。比如,基础研究特区的项目周期达5年甚至10年,可以免除其“后顾之忧”,避免”卷”在项目申报与评审中。
记者:您曾在硅谷、深圳这些国际科创中心工作过,您观察到这些地方的人才生态有什么独特之处?对我们上海有什么启发?
陈海波:我2008年在硅谷交流时就发现一个现象:周末的湾区小餐馆、咖啡吧里有很多“组局”,在高校学者或创业者身边可能就坐着上市或待上市公司的创始人,他们之间不按身份“三六九等”划分,更像一群“聊技术”的朋友。这种非官方、比较“松弛”的交流形式,并无严密组织,反而能让想法自然碰撞。我201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作访问科学家时,也能常见大学里有企业大佬走进课堂来作报告,并在报告后与学生们深入交流。
深圳在市场导向创新路径、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大科学装置投入,以及开放人才政策等方面的探索,也值得借鉴。我们要更好地平衡“放”“管”“服”,在适当场合营造创新创业、投资融资的“氛围组”,不必过于“高大上”,而让科研一线的年轻人也能参与。让创新的人自然聚集,让想法自由流动,提升对失败、失误的容错性。

练秋湖畔。徐瑞哲 摄
记者:您长期主导高校和企业之间的跨界合作,这种“无界”的产学研模式,是否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成为常态?
陈海波:从原始创新到重大产业突破,单靠高校很难完成,应当与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更紧密、制度化的合作。现在行业龙头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在普遍提升,所以研发资源会更多地在高校和企业间双向流动,也就是“高校人员进企业”与“企业人员进高校”。
开放心态、打破创新边界,相互融合,才能一起打通体制机制的“卡点堵点”。例如,上海交大刚成立一年多的人工智能学院,打造了“3-3-3”的多元差异化引育格局:1/3老师来自海外顶尖高校,1/3来自国内一流院校,1/3直接从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引进。
最近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学院青年团队发布的全球首个端侧原生大模型就是成果之一。这个大模型能够更好地克服端侧设备硬件资源小等约束,能够用于打造AI电脑、AI手机、智能座舱、AI眼镜等,不用联网就能够在端侧实现接近云端智能的水平,并支持打造端侧智能体,从而更好地保护用户数据隐私,减少云上AI调用成本,降低时延等。
记者:您提到校企打破边界、双向合作,这种跨组织机构的创新,是否也体现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上?
陈海波:跨学科交叉研究是大势所趋,仅以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为例,我们已经看到了跨产业、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比如“IT+BT”,也就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协同创新。例如,我所带领的上海交大并行与分布式系统研究所(IPADS实验室)与转化医学研究院执行院长樊春海院士团队就在深度合作,开展DNA数据存储方面的研究,涉及核酸化学生物学、核酸信息材料等多个领域。
在上海交大张江高等研究院,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中心到DNA存储研究中心,七大中心基本都是学科交叉的“试验田”。在此,我们正联合攻关的“AutoDNA”,是一个能够连续作业96小时的自主核酸实验室,可以不断攻克DNA样片“出片”易错的难题。期待这类非硅基的计算与存储,未来能够实现颠覆性的突破。

访谈陈海波教授。徐瑞哲 摄
原标题:《AI时代,自主构建一到两套生态体系,相互之间都能“讲普通话”|专访陈海波》
均 徐瑞哲 摄
题图说明: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
作者:解放日报 徐瑞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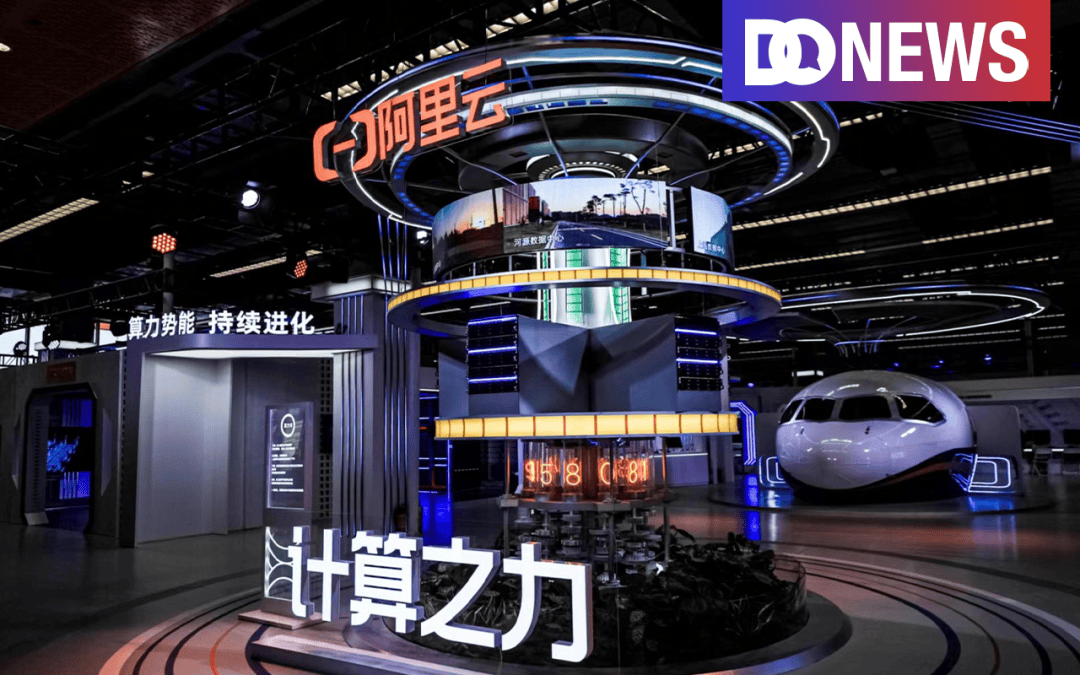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