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业竞争从不容情,但历史应当铭记:没有昨日的供应链协同,就没有今日的智能汽车革命。”
作者丨李雨晨
编辑丨林觉民
在2021年开启名为“卫城计划”的智驾自研之前,理想的智能驾驶曾有几个关键的托举者。
2019年,理想One这款决定命运之车的成功离不开易航智能——当时,这是造车行业内唯一量产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
然而,到了2020年,所有人都在期待理想与易航智能再续前缘时,理想却突然选择了尚处于“黑暗”中的地平线。
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车企自研路线与以Mobileye为代表的强势供应商的冲突。身处主机厂与芯片商的博弈漩涡中,中小智驾Tier1公司力图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更多的主动权。
01
互相成就的行业佳话
值得称道的一点是,理想在易航智能只有4个人时就选定了合作。周围人对CEO陈禹行的评价是:头脑聪明、有眼光。2015年易航智能成立时,百度的智驾团队还没成为业界的黄埔军校,国内智驾公司极少,能先于行业看到机会,确实需要远见。
当时的智驾公司大部分是从L4起家,因为做L4能带来高估值,便于融资。易航智能却选择了渐进式的智能驾驶路线,先从L2+的量产做起。
后来,陈禹行结识了明势资本创始人黄明明。黄明明给了陈禹行一个月时间。2016年7月,长春,易航拿着一辆马自达6进行改装,搭载了易航开发的智能驾驶功能。
当时,参加试驾的有四个人,陈禹行、李雪峰、王春有以及史艳辉。这趟车从长春开到了沈阳再开回去,接近1000公里,体验感非常不错,易航还解决了很多公司解决不了的方向盘抖动问题。
路测结束的第二天,黄明明就给理想汽车(当时还叫车和家)创始人李想打了一通电话(两人的私交较好)。接下来,明势资本、理想汽车、易到创始人周航共同参与了易航的天使轮投资。2016的下半年,易航的估值达到了4800万人民币。
据接近易航的人表示,“理想给的估值与融资金额都不是最高的,易航有其他渠道可以拿到更多的钱。但易航选择理想,最关键的是可以接到理想的项目。”
到了2017年春节前,易航又完成A轮融资,由经纬中国和华夏幸福所属的基金共同参与。从估值4800万人民币,到估值6个亿,易航只花了不到6个月。再后来,源码、中金和广汽投了易航的B轮,估值猛涨到了20亿人民币。
估值如此之高、融资如此之速,离不开易航的创始人陈禹行。
陈禹行是吉林大学车辆工程与控制毕业,去伯克利做过一段时间访问学者。李想欣赏西安交大少年班出身的陈禹行,很聪明、有想法,想把易航纳入自己的供应商体系。
易航的招人条件非常严格,不看特别漂亮的简历,但从博世、恒润挖了很多人。2017年中,易航的核心班底初步建成,在朝阳区的电通创意广场找了一个约60个工位的办公室。因为这个位置在五元桥附近,离理想很近。
从2017年初开始,易航的员工就拿着理想的工牌、在理想参与考评、在理想的食堂吃饭、参加理想的年会。甚至,易航的几位高管还印了理想的名片。在2018年之前,陈禹行兼着理想智驾负责人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这段时间里的易航就是理想的“智驾部门”。
后来,随着规模扩大,不少供应商、合作伙伴、投资人来访,易航又重新找了新办公室。
易航真正的声名鹊起是在理想One。据知情人士透露,“理想One前5万台车的智驾是易航做的,后来是理想内部自己做。”
理想One智能驾驶的量产,易航帮忙完成了两件关键大事:首先,李想不是把理想One的智能驾驶全部托付给易航。一开始,只是想让易航负责上层的算法部分,硬件加底层软件由另一家供应商来负责。
这时出现一个插曲,这家供应商做了一年之后,其美国总部进行了战略重组,砍掉了智驾功能业务。当时的理想还远未达到今天的规模,经过评估后,供应商决定不再服务理想。易航承担了临时救火的角色,将硬件和底层软件全都接过来,完完全全变成理想的Tier 1。
其次,2019年年初,Mobileye的方案中有一款摄像头,是三星旗下一家做汽车电子的公司来供货。但是经过长达数月的商务谈判,最后合作告吹。
这时候,距离理想One的量产时间仅仅只有9个月。
可以说,易航创造了一个奇迹:ADAS智驾摄像头最快的开发时间也需要一年,易航仅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而且,易航有一个摄像头组装的设备,这个技术只有美国才有。易航的供应商需要报关,当时为了抢时间,供应商自己去香港“人肉”带货。
如果没有易航的两次临危受命,理想One的智驾功能就没有办法顺利量产。在当时凶险的竞争环境下,理想汽车的存在与否都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易航也要感谢理想。
早期,易航智能虽已具备全套解决方案,却没有供货权。因为要快速量产,最终选择跟以色列的Mobileye合作:基于Mobileye的芯片,易航做后面的规划、控制等功能模块。
Mobileye最早在国内的代理是经纬恒润,易航与Mobileye的组合,功劳在于理想前高管沈亚楠的引路。
沈亚楠1977年生人。据说,李想和沈亚楠两人在北京欧陆广场的星巴克里,聊了一个小时就达成一致见解。加入理想后,沈亚楠就带着陈禹行等一共5人到了以色列,还见到了创始人Amnon Shashua。
当时正是Mobileye的巅峰时刻。一位易航前员工表示,”当时易航才几十号人,怎么可能成为Mobileye的Tier1呢,当时Mobileye牛的不行。“
但是,沈亚楠把合作的事情谈成了。接近沈亚楠的人表示,“商务谈判能力很强,英语非常流利。当时好多供应商在Mobileye办公室门口排着队,沈亚楠在谈判过程中的反应很快。”
最终,在理想的帮助下,易航顺利与Mobileye达成合作,通过理想One这一案子,跻身国内头部Tier 1厂商行列。
02
理想与Mobileye的暗战
如果易航可以与理想一直走下去,应该能够成就一段佳话。只是,事与愿违。
2019年12月,理想ONE正式交付用户,一炮而红。一年之后的2020年底,理想和易航沟通,想在原有辅助驾驶系统的基础上升级一个更复杂的NOA方案,并将原计划在2021年7到8月交付的2021款理想ONE提前到6月份。
业内流传的一个说法是,为了加快智驾开发进度,理想CFO李铁曾找过易航智能,想要理想One智驾的源代码,被要了天价。实际上,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有接近双方沟通细节的人士向雷峰网表示,“陈禹行并没有报高价,而是由其他高管和理想方面进行的口头沟通。易航还没有牛到可以和客户叫板的程度。且当时理想内部也在讨论供应商模式和自研模式的两条路线。”
易航与理想的逐步疏远,其根源在于芯片商Mobileye的一系列规定——李铁要想的那套源代码,是理想带领易航前往以色列得到的授权。
合同中约定,所有与Mobileye相关的东西只能留在与其合作的Tier1里,不能外传。
更进一步的细节是:Mobileye先提供芯片,后续硬件的原理图Mobileye要审核,通过之后才可提供给最终客户。另外,Mobileye的软硬件是绑定的,包括信息的传输形式等都不能外传。
即便是易航能提供后端的规划、控制软件,前端的感知数据仍然掌握在Mobileye手中。
在2019款理想ONE上,易航给理想提供的硬件是“一个域控制器+一个摄像头”的组合,当时是出于稳定性的考虑。虽然这种形式会提高成本,但是基于这个组合可以提供行泊一体的功能,整体而言更有性价比。
等到2021款理想ONE改款时,硬件方案的改动涉及“数据外流”,会触碰到Mobileye的雷区,存在断供和赔偿金的风险。
有知情人士表示,“理想提出改硬件的需求时,易航与Mobileye的商务合同已经敲定,这是一个以项目为核心的采购协议,易航每用到一个客户身上就要与Mobileye签一次协议。隔着Tier1,Mobileye的强势程度,理想的感受可能没有那么深。”
一个是重要客户,一个是核心供应商,易航智能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因为同期易航还接了上汽的Mobileye项目,无法与Mobileye划清界限,权衡之下不得不放弃理想的需求。
后来,沈亚楠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智驾上的一部分核心能力没法积累,所以我们选择了更加开放的平台,像地平线。”
这番话,暗指的就是Mobileye。
后来,Mobileye的一位高级副总裁紧接着也在采访里隔空喊话:“中国一些造车新势力,其实不懂智驾行业。”
另外,理想的一个学习对象是特斯拉,为了自己的车能够有更多的“特斯拉”味,从2018年开始,理想着手建立数据闭环体系,由郎咸朋牵头,以真实的道路数据进行快速的算法纠错与迭代。
这个方式无疑是绕开Mobileye自建感知能力。为此,在一次谈判中,Mobileye非常紧张并带有“威胁”的意味向理想交涉:“如果你们还希望我们提供芯片,那就把你们车上的摄像头拿掉。”
发现硬件并行的方案行不通时,理想紧急制定Plan B,地平线及时出现并且接下了这一重要任务。
从具体分工看,J3的感知部分是地平线负责,规控部分由理想内部团队自研。那时候,理想只需要一种类型的公司,就是做硬件的公司,但这既不是易航擅长,也不是易航的战略方向。此时的易航已经深知Mobileye的局限性,开始着手建立感知乃至全栈自研的能力。
地平线接下理想的案子时间很紧,只有8个月的时间。
理想的目标很明确:2021年7月份港股上市,上市的时候一定要有爆款车型支撑基本盘。
为了及时响应理想的需求,余凯牵头动用了地平线的全部精锐,组建了一支300人的团队派驻理想,实时提供协助。在当时已经经历了大瘦身的地平线里,这几乎占据了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甚至为了配合理想的新车倒计时,地平线团队陪着理想汽车团队不分日夜的加班调教芯片,就连李想本人都多次对地平线团队拼命般的工作态度大加赞叹。
对于地平线的支持,理想也给予了回报。2021年,理想One、L7 等车型上首发地平线的J3芯片。
03
没有供应链协同,就没有智能化革命
度过最难的一关之后,理想依靠“奶爸车”的概念切中市场,逐渐进入上升通道。
2022年,理想开始启动伊利亚特计划,在L9车型上交付Orin X项目,用纯视觉方案做盲区检测、避障等功能。和伊利亚特计划同期的是,贾鹏开发基于地平线J5的Pro平台,这个项目被称之为奥德赛计划。
2024年,理想开始了端到端项目的开发,被称为达摩克里斯计划。2024年11月28日,理想就向智驾Max版用户全量推送了端到端+VLM双系统架构最新成果——车位到车位,成为行业首个全量推送这一功能的车企。
随着新车型i8发布,理想成为全球第一个展示VLA辅助驾驶大模型的车企。在自研路线的推进下,理想逐步走向智驾第一梯队。
易航与理想的合作翻篇之后,陆续与几家车企达成或接近达成深度合作。
2021年3月,易航就已完成了城市NOA的功能开发。威马曾宣称智驾供应商是百度,其实是易航。威马只用了百度的泊车能力,没有和外部公布与易航的合作关系。
这一逻辑也好理解,主机厂对外都宣称是全栈自研,不愿意对外露出供应商。除非是华为、百度、大疆这类品牌力足够的厂商,才有为主机厂营销造势的能力。
易航另一个接近合作成功的车企是比亚迪。
2019年理想one量产之后,易航开始接触比亚迪,与比亚迪的十五事业部合作了一个泊车项目。当时,TDA4是业内智能驾驶方案的主流,但是易航与比亚迪的项目用的是TDA2的芯片。做了这一单之后缺乏复制性。所以,易航在比亚迪这个项目上没有投入太多精力。最后,易航将项目的代码卖给了比亚迪,拿回了一些辛苦费。
易航还有一个合作伙伴是,广汽。
2019年3月,易航获广汽资本旗下基金1亿元B+轮投资。广汽曾经和易航智能探讨过两次泊车项目。但是项目没有推进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广汽希望用TDA2做一个泊车项目,但当时易航正在全力做TDA4,就选择性放弃。后续广汽又论证了基于TDA4开发的可能性,但最后不了了之。
第二,广汽内部研发力量林立。广汽研究院、广汽乘用车以及广汽新能源(即埃安)都均有话语权。
有前易航员工回忆,“有一次广汽浩浩荡荡来了30多人。易航的办公室都坐不下。每一波人都发表观点,最后谈成四个车型、100万开发费。但是要求所有代码全交,但关键这些车型只是选配,易航还得给广汽培训。这完全干不下去,收益基本为0。”
2021年底,智驾行业陷入一段时间低谷,财务投资变得更加谨慎。后来,易航拿到了北汽的股权融资,也积极推进与北汽的项目合作。
据雷峰网了解,易航与北汽研究总院合作,北汽通过研究总院的量产项目都优先考虑和易航合作,双方在核心项目上采取联合开发的模式。北汽在智驾的经验积累不够多,这样就能和易航共享平台。
第二,北汽给了易航智能不少平台化的产品,进一步帮助易航提高经验的复用率。
易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是上汽大通。上汽大通几乎把全量车型的项目交给易航, 只要上汽大通有自身的新规划,都会选择易航作为供应商。 此外,还有江铃雷诺的项目。江铃雷诺的车主要用于出口,让易航打通了出口的这条路径。
回到理想与易航的合作往事。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历史上,供应商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智能驾驶尤其如此。
直到现在,理想仍然是易航智能的重要股东之一。这也说明,理想与易航并没有产生外界所认为的巨大分歧。双方的分手,核心仍是车企自研路线与芯片黑盒模式的主动权之争。
早期,对智能化认知不足的车企,依靠供应商的方案快速搭建起智能化的门面。这段合作史中,技术转移与市场教育同步发生:供应商教会车企如何定义用户需求,如何搭建算法框架,甚至如何应对消费者的第一波质疑。
商业竞争从不容情,但历史应当铭记:没有昨日的供应链协同,就没有今日的智能汽车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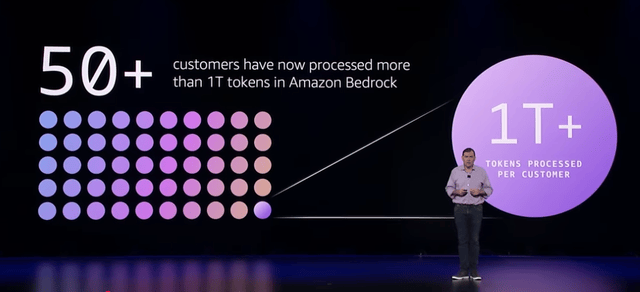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