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形机器人赛道火出圈,但能赚钱的没几个。
绝大多数机器人仍在寻找“被需要”的场景,包括宇树。租赁展演市场,成了它们暂时的去处。
这些机器人被运往婚礼、商场、展销会与企业年会,当花童、献才艺、做迎宾。穿着大花袄转手绢只是“基操”,为了吸引顾客,它们不断打磨才艺——会跳科目三、社会摇,甚至能川剧变脸。
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像流浪的临时演员,四处跑龙套、反复被租赁。有种黑色幽默感。
但换个角度,这既是一门生意,也是一场探索。AI机器人商业化的路依旧漫长,租赁其实是寻找落地的机会。
那些穿梭在婚礼与商场间的租赁商们,让机器人有了可见的使用轨迹,进入真实生活场景。在AI商业化的早期,他们是为技术“找场地”的人。
阿猛就是其中之一。今年3月,他察觉到这股商机,入局机器人租赁生意。科技像魔术一样落地在他的世界里,每一场演出、每一笔订单,都像是他与未来赛跑的证据。
只是,风口生意也存在阴影。高光过后,泡沫渐散,从业者蜂拥而入,价格被层层压低,竞争愈发激烈。
短短几个月,阿猛亲历了行业的波荡起伏,以下是他的自述。
 行走的排面
行走的排面按下遥控键的瞬间,机器人微微一颤,仿佛被注入了灵魂。紧接着,它一个利落的前滚翻,跪地、旋身、再弹起,动作流畅得像受过训练的杂技演员。
围观的老人们先是愣了几秒,随即笑得眯起眼,拍手叫好。
这是我最近带着宇树机器人,在北京一家养老中心做现场表演时的情景。
这几年,“智慧养老”成了热词,许多机构主动联系我,希望用机器人表演增添活力与科技感。
我带来的这台宇树机器人,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人少的时候,它被安排在门口迎宾,机械手臂不停挥动,热情地向路过的老人打招呼;等人多起来时,它又立刻切换模式,在大厅里跳舞、扭腰、敬礼,为养老中心带来了热闹与人气。
眼下,人形机器人虽尚未真正服务于人类生活,但在“制造科技感”和“撑场面”方面,发挥到了极致。也正因如此,我们这行才应运而生。
做机器人租赁展演这半年,我发现客户大都有类似需求:他们希望借助人形机器人,为企业营造科技感。不论是开业还是展销,机器人出场,就是行走的流量。
不过,由于造价高昂、产量有限,不少企业的使用需求又相对零散,于是租赁成了更现实、更划算的选择。
生意的本质,就是满足需求。作为最早一批入局者,我察觉到了这股商机。开始尝试在机器人厂商和企业客户之间穿针引线,做那个缝合两端需求的“中间人”。
做机器人租赁之前,我原本是一名电商从业者,人工智能与我的生活几乎没有交集。直到今年3月,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一场直播。
直播间里,主播操控着一台宇树机器人,只是让它简单的在地上行走、上床平躺,就吸引了近万人围观。
我查了查资料,才知道宇树机器人是今年春晚的“明星”。它们穿着大花袄跳舞、打滚、转手绢,一夜之间成了全民话题。那一刻,我意识到,这或许是个巨大的风口。
私信主播后,得知那台机器人型号是宇树G1,官方售价9.9万一台,但要等两个月才能交货。主播手里有现货,但要昂贵很多,售价18万一台,若选择租赁价格是1.2万一天。
我立刻意识到,现货在这行是稀缺资源。能拿到机器人的人,就像掌握了淘金的铲子——既能高价出租,也能倒卖赚差价。
我没有立刻买机器,决定先试着做中间商,倒卖一单看看行情。
我模仿同行,在网上发了一条“宇树机器人租赁服务”的帖子。两天后,就接到一家商场的活动咨询。他们的要求很简单:让机器人站在门口挥手迎宾,报价9000元一天。
我爽快接下,又立刻发帖找人接单,打算以7000元的价格外派给有现货的同行。这一单不为赚钱,只为摸清行业链条的每个环节。
在与同行交流的过程中,我被拉进了一个全国性的机器人租赁群。群里聚集着各地业务员,消息更新灵通。进群当天,一个杭州的同行就接下了我的订单,并邀请我去他公司实地查看机器。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机器人“本尊”。
一个带轮的黑色箱子被推到我面前,宇树机器人弯着腿蜷缩在里面,两只脚搭在肩膀上,看起来有些滑稽。
工作人员取它出来的过程,像是在抬一个沉睡的人。四个员工分抓四肢,还有一人托着头,几人齐力把它放到地上,调整好姿势,按下开机键。
两分钟后,刚刚还“毫无生气”的机器突然亮起了脸部灯光。它先是微微蜷腿,继而撑地起身,像被注入灵魂般自己站了起来。紧接着,它朝我走来,步伐稳健、气势逼人。
我被震撼了。
后来我请那位同行吃饭,系统地学习了一遍机器人的操作流程。原来,宇树机器人分为基础款和二次开发款。前者只能做挥手、握手、转身等几个标准动作;后者则能根据客户需求定制行为脚本,售价自然更高——当时官方报价24.9万一台。
但无论哪一款,操控都比较简单,只需通过遥控器下达指令,就能完成整套动作。
我意识到:这一行的技术门槛没我想象的高,关键在于谁能抢到订单。
我在电商行业摸爬滚打近十年,对互联网投流、引流逻辑再熟悉不过。粗略算了下,当时机器人租赁的市场价约一万元一天,接十单左右就能回本。于是我立刻在宇树的线下官方门店下了订单。
等待机器交付的两个月,我继续做中介接单,一边熟悉业务,一边积累资源。当时每台机器人的租赁价稳定在一万元左右,机器狗的租金则在三千上下,且能拿到现货。我便又入手了四台机器狗组合接单。
那段时间,订单源源不断。平均两三天就能接到一单,靠着差价,我一个月能赚三四万。
 图 |阿猛的机器人在西安长城文化节演出
图 |阿猛的机器人在西安长城文化节演出 江湖艺人养成
江湖艺人养成机器人第一次帮我拿下大单,是在五一假期前。
那时距离放假还有三天,我在社交媒体上接到一家大型超市的咨询。对方想在节日期间举办一场热闹的“科技表演”——要我安排一台机器人和四条机器狗,现场表演川剧变脸。
我愣了几秒。看来,那些只会挥手、敬礼的机器人,已经满足不了人类的胃口了。现在,它们不仅得有才艺,还得拿得出绝活。
虽然这个需求让我有些意外,手上那台新订购的机器人也还没到货,但我还是当机立断地接下了订单。
根据群里的派单消息,我知道那段时间能调动的现货极少。而企业的节日活动通常要提前筹备,从时间节点看,对方显然很着急。
五一这种黄金档期,客户选择少、预算又充裕,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我果断开价:三万二一天,八天活动,总价二十四万。
即使在节日,这个报价也高于了当时的市场均价。没想到,对方几乎没犹豫就同意了。
拿下订单后,我立刻在群里寻找能“顶班”的机器人。一位杭州同行有现货,报价十六万。我咬牙买下。虽然比官方价高出近七万,但这笔大单给了我信心——照这势头,三四单就能回本。
拿到新机器人后,我开始带它“拜师学艺”。
当时同行里能让机器人变脸的不多,偶尔有几个掌握诀窍的,也都守口如瓶。最终,我在社交平台上花了5000块,找到一位四川变脸师傅,愿愿意传授几招。
视频连线那天,我把机器人搬到镜头前。师傅第一次收“非人类弟子”,神情有些复杂。
他告诉我,变脸的核心在“扯脸”:每张脸谱后都藏着一根细丝线,连接到衣服的隐蔽处。演员趁动作间隙一拉丝线,脸谱就能迅速脱落。
这动作需要极高的灵敏度和时机感,而机器人手脚僵硬,根本不可能完美完成。最后,我只好定制了一个微型电动装置,装在机器人肩后。只要它挥手,装置就能带动丝线,完成“变脸”的瞬间。
那两天,我带着机器人对着音乐反复排练了二十多遍。每次看着它披上大袍、换上面具,我都会在脑海中想象观众围观的热闹场面,心里也跟着激动。
 图 |阿猛在家跟机器人练习川剧变脸
图 |阿猛在家跟机器人练习川剧变脸可真正上场那天,我才明白机器人的“艺人之路”有多难。
演出地点在超市中庭,几排货架交错出的狭小空地上,机器人披袍戴冠地站着,周围是五颜六色的促销海报。川剧变脸的鼓点一响,本该恢宏的气势,却在超市的背景音里显得有些突兀。
但机器人依旧一丝不苟地完成每一个动作。它从粮油区走到家电区,随着节奏挥手、转身、变脸。渐渐地,原本稀稀拉拉的观众围了上来——孩子拍手欢笑,老人举着手机录像。
那一刻,我有点被打动。我想,这种信念感,大概只有机器人才能做到。
那场演出之后,“机器人变脸”成了我的独门节目。
我带它参加过机器人文艺晚会,站上真正的大舞台。灯光亮起,音乐一响,它披着锦袍、面色冷峻地立在舞台中央,比人还威风。
后来,在接各类甲方需求的过程中,我又入手了能二次开发的EDU款机器人。它们的“技能树”越来越丰富。除了川剧变脸,还能跳新疆舞、查尔斯顿舞、社会摇。客户要什么,我和机器人就练什么。
有次赶上下雨,机器人披着透明雨衣,在湿滑的地面上继续热舞;还有客户要求机器人“飞上天”,我就想办法用无人机把它吊到几十米高的楼顶上空旋转。
那时,我们几乎跑遍了各种场合:国家级赛事的暖场嘉宾、企业年会的压轴节目、学校运动会的方阵表演,甚至养老院的广场舞和民俗演出。
机器人能登大雅之堂,也能混迹市井街巷。我常开玩笑说,它比我还懂生活。
只是,当我以为这行会一路高歌时,意外还是来了。

6月初,群里有人派单,一台机器人配一只机器狗,共5000元一天。
我看到后,和几个同行在小群里吐槽“价格跳水”。那时,机器人五六千一天、机器狗两千,已经是我们心里的“底线价”。
没想到,很快就有人在群里回道:“3000一天可接。”
这句回复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整个群。有人斥责“恶性竞争”,有人劝“别拉低行情”。可价格战,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其实,在我购买EDU款机器人时,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官方售价24.9万的机器,代理商居然能便宜不少。原因很简单,库存滞销。与此同时,宇树的交货周期也在缩短,从两个月变成了不到一个月。
不只是宇树。智元、众擎、松延动力等品牌的机器人也开始进入展演市场。现货不再稀缺,新的从业者一波接一波地涌进来。
我还记得三月份时,群里一条派单消息,只有三四个人回复。到了六月,同一条消息下已经有十几人抢单。我微信里的行业群,也从最初的三四个变成了十多个。
一个同行和我差不多时间入行。看到势头火爆,他一口气买了七八台机器人。可到了五月底,订单骤减,他急着回本,只能低价出租、甚至转卖。
不止租赁市场在降温,整个行业都在下坠。刚入行那会儿,给机器人“编一支舞”的二次开发价格要六七千。到五月后,这个价格一路滑落,如今几百块就能买到“动作模板”。
同行们为了拓展客源,开始挤向社交媒体直播。可机器人能带来流量,却不一定带来订单。
有个朋友每天带着机器人在西湖边散步,边直播边招揽生意。两个月下来,涨粉十万,却没接到几单。
有一次,他让机器人跳二次开发的舞蹈,过程中机器人踩到石头摔倒,当场断了腿。那个月他没赚到钱,却花了一万多修机器。
还有人天天拍机器人的短视频,换各种造型拍跳舞、做特技。机器人火了,品牌火了,但他们的账户却始终入不敷出。
最终,许多机器被过度使用、磨损严重,只能折价卖出,或者干脆拆成零件处理。
经过一轮低价竞争,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十一。我也以为能像五一那样再爆一单。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被截胡的结果。
那时,一家合肥的机关单位找我,要三台机器人、三条机器狗,在公园搞活动。我心里预估的价格是机器人每台2万一天,机器狗每只2000一天。
可对方一开口,直接把我心理价砍了一半:“机器人和机器狗一起,一万二一天。”
想到这是少有的旺季,我尝试把价抬到一万五。对方说要“请示领导”,让我等消息。
两天后,我忍不住去问,得到的只是模糊的回复。
直到国庆当天,我刷到对方的朋友圈,看到他们口中的“机器人表演”果然如期举行。只是,公园里跳舞的,不是我的机器人。
那几天,我又接了两单咨询,最后都因为价格没谈拢而告吹。
赚钱之外,我更难过的是,行业变得越来越“廉价”。
每一场活动,我们都在尽力做到最好。我总是提前一天去踩点,根据客户的需求调整动作和灯光,让机器人在镜头前表现得更“像人”。
每次表演都能吸引观众驻足,有的企业还因此上了地方媒体。但这些努力,在价格战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
一次带机器人外出表演,我算了算账:抛去住宿、路费,现场还得请兼职帮忙操控,成本至少上千块。高铁票买不到,还得坐飞机,托运机器人的费用比机票贵两倍。
若机器人在表演时摔倒、卡机、趴窝,不仅要赔客户的钱,还得自掏腰包维修。给机器人“治病”,比给人修骨头还贵。
今年八月,我的两台机器人去了新疆,参加亚欧商品贸易博览会。
那是我第一次参与全国大型机器人演出。几十台机器人在舞台上整齐地挥动手臂,银色的外壳在灯光下闪烁,台下观众屏息注视。
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骄傲。我为国家的科技实力自豪,也为自己能亲历这场智能化浪潮而由衷高兴。
 图 | 10月,阿猛在杭州参加机器人文艺晚会
图 | 10月,阿猛在杭州参加机器人文艺晚会作为租赁商,我们虽然不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却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冰冷的科技找到了接地气的舞台,也让普通人近距离接触到了这些高科技产品。
所有新兴行业,在热潮退去后,都会不可避免地进入洗牌期。哪怕风口散去,租赁生意陷入内卷,我仍觉得这半年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至少这半年里,我和我的机器人们,都在认真地工作,也在认真地生活。(AI故事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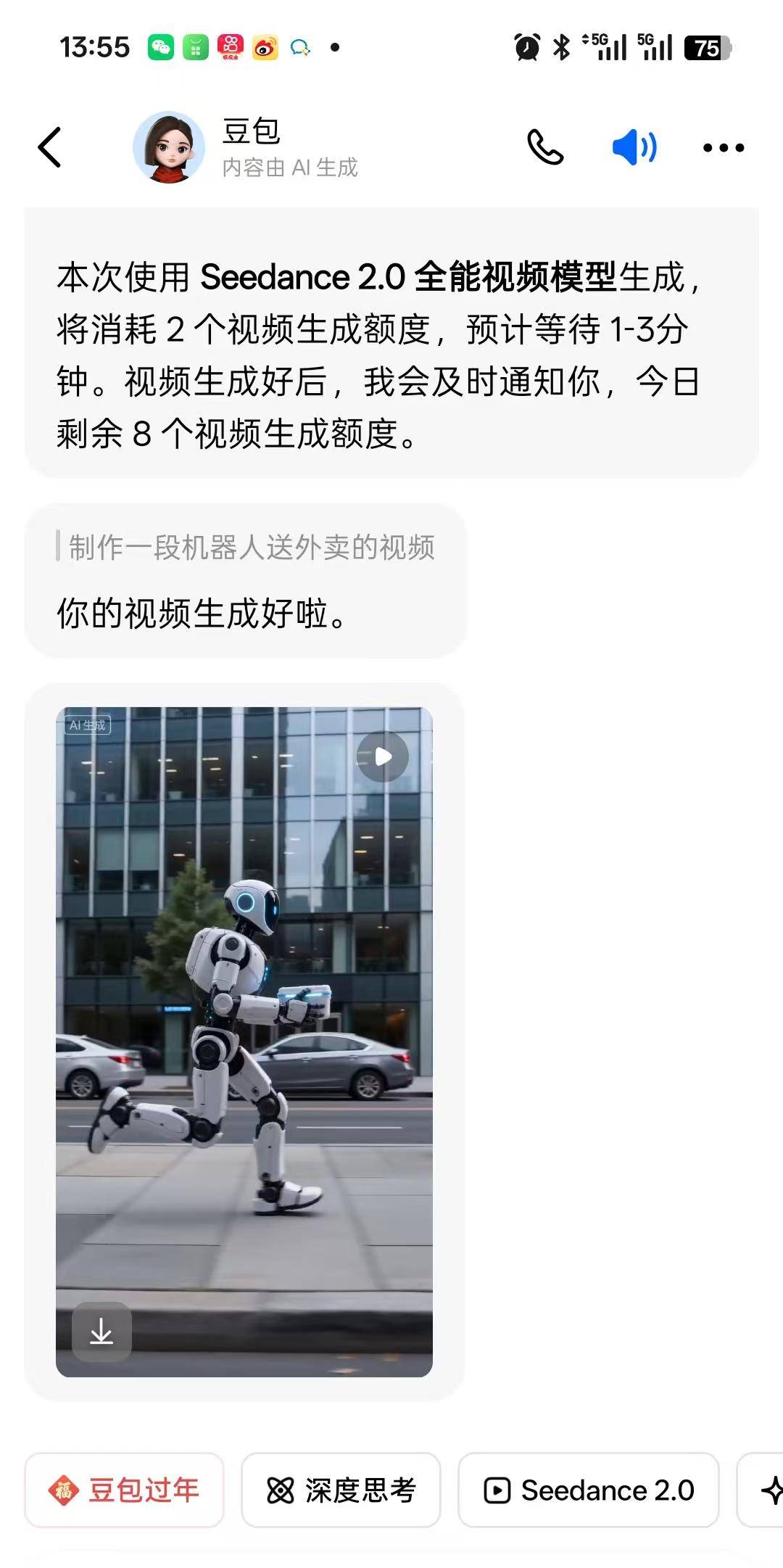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