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选择农业时,我们早已是被技术重新组织的生命。
一次普通的回家之路,我的电动车电量从50%到闪红警告迅速下坠,雪后即将日暮,在一条鲜少人经过的乡村小路上,瞬间蒙受的压力我感到非常焦躁。
读数、概率提示、算法生成的剩余可能性,是否已经构成了现代情绪的控制机制?来自技术的风险预判隐晦地提示着人会面临的危险和困境。在低头看向数字面板的短短几秒中,人不再根据身体经验判断距离与体力,而是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这个隐藏逻辑的量化系统;焦虑、恐惧、不信任,都是系统提供的,技术是不是现代的幽灵?

如果房屋可以被理解为人类身体的外化,那么技术是否也可以被认作人类大脑的义肢?但现代的技术更像是一个自治的环境,黑箱中的数字和概率重新配置着人的感知和行动。我们会经历非常多的“电量闪红”的时刻,技术系统向主体发出的“你已越界”或“你已不足”的评判,持续地制造着主体脆弱感。
斯蒂格勒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指出,技术作为外化记忆和社会组织机制具有药性:它既是解毒剂,也是毒药。然而,随着算法、平台经济与风险社会的全面铺开,斯蒂格勒式的技术药性已从抽象理论变成日常经验。这一判断是否已经形成了某种理论的宿命论?是否存在其他哲学路径可以真正思考如何从技术决定的生活环境中重新找到主体性?或者说,我们是否需要重新理解主体性本身?
关于如何突破这种技术药性的讨论一直试图打破“技术的毒只能由技术来解”的闭路逻辑(Stiegler, 1998)。这个问题并不只属于技术哲学,它贯穿政治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进入生态危机与现代性反思的核心。
如果从更漫长的历史尺度来看,人类在选择农业的那一刻起,便进入了不可逆的路径:选择意味着放弃,进步意味着耗损,技术的扩张意味着依赖也已形成。这是既成的结构事实,现代技术的困境不过是这一长链条的最新形态(Diamond, 1997)。
从电动车没电这样普通的日常体验出发,本文聚焦技术的监控性、警告性与不透明性如何塑造了新的生活现实。同时,我们也可以重新审视斯蒂格勒的技术药性理论在今日是否已作为现实,以及它是否被其他哲学路径所补充、修正或超越。在一个以数字化焦虑为底色的时代,我们究竟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所谓摆脱技术或改造技术的可能性与限度?
第一部分:数字化警告——作为习惯的生活
我们今天面对的技术压力,往往并不以直接压力的形式存在,它来自更难拒绝的形式——警告。电量不足的闪烁提示、健康应用推送的异常指标、地图导航反复计算的抵达时间,“尽责”的提醒让人觉得自己在被服务着:你正在接近某个临界点。
技术逻辑的变化与早期工业社会中明确的规范和纪律不同,当代技术更倾向于以风险管理的名义介入日常生活。它将未来的失败、耗尽或危险提前可视化,并以数字的形式呈现在行为主体面前。人被训练到在尚未真正遭遇困境之前,就已被置入了预期的紧张状态之中。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技术的核心功能是设定阈值。阈值并不具有道德意义,它只是一个中性的提示,但正是它重塑着主体的行动逻辑。人不再问“我是否应该继续”,而是反复计算“我还能坚持多久”。比如电动车电量骤降,并不意味着行动在物理上立刻变得不可能,但技术已经在情绪层面宣布了不足的状态。
不足提示所引发的焦虑,并非源于这种状态的不确定性,而恰恰来自过度的确定。数字化系统通过精确读数,替代了模糊的经验判断。主体被迫相信系统所呈现的概率、剩余量和风险预测,却很少有人去理解这些判断是如何生成的,技术隐藏了自身的推理过程。精密技术和科学化的包装,也让人相信自己在计算和读数方面不如它们。在这一意义上,技术的真正问题应该是不透明。
当技术系统成为判断者,主体的位置也随之发生变化。人还是密林中或草原上依靠经验和身体感受来估算距离、体力与风险的行动者吗?还是变成一个不断接受评估的对象?每一次查看屏幕,都是一次对自身状态的外部确认。焦虑、怀疑、恐惧,是这种评估结构稳定汇报并送达的情绪结果。它不断强化一种脆弱感:你是有限的、随时可能耗尽的、需要被持续提醒的存在。技术不再只是辅助行动的工具,它已经作为主体理解自身状态的主要媒介。
因此,现代技术经验的关键转变在于:生活不再只是被组织,而是被持续评估。主体不再面对明确的禁令,而是被包围在一整套关于剩余、风险和可能性的提示之中。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并非被剥夺行动能力,而是被不断提醒自身的不足。这正是数字化警告体系最深层的效应——它将生存本身转化为一场关于阈值的管理。
第二部分:技术药性之后——三种理解技术困境的哲学路径
当数字化警告成为现代普遍的生活经验时,我们很容易将问题归因于“技术滥用”,只要修正使用方式、提升系统理性,问题会不断消失。但这一判断是否过于乐观?事实上,关于技术如何塑造主体、是否存在可逆的出路,早已是20世纪技术哲学中长期讨论的核心问题。
斯蒂格勒对这一问题的贡献在于,他拒绝将技术理解为中性的工具或单纯的外部环境。在他的哲学中,技术被界定为人类记忆、时间经验与社会组织的外化形式。从书写、机械到数字系统,技术一直在重新分配人类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技术并非侵入生活的异物,从人类制作第一件工具开始,技术已与人的存在结构纠缠在一起。
斯蒂格勒提出了著名的技术药性概念。他认为,技术既是解毒剂,也是毒药。一方面扩展了人的能力,使复杂社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可能剥夺主体的判断力与行动能力,造成去技能化和去个体化。真正的问题在于技术被何种力量主导、如何被社会组织。斯蒂格勒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由资本与算法垄断的当代技术体系(Stiegler, 2010)。
然而,他的立场也内含难以回避的紧张关系。既然技术本身不可避免,且早已构成人类存在的条件,那么技术带来的问题似乎只能通过“更好的”技术来修复。这在逻辑上形成了闭环:技术的毒,最终仍需技术来解。数字化警告体系的扩张,正是在这种逻辑中不断被合理化:如果焦虑是问题,那就引入更精准的风险评估;如果系统不透明,那就设计更友好的界面。斯蒂格勒的技术药性理论,经过二十余年的学术传播与公共讨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对技术问题普遍认同的理论框架:无论是政策设计、企业管理或者媒体话语,“技术既有毒性又可解毒”的思路,几乎成为了分析技术焦虑与治理的显学。
与斯蒂格勒将技术视为“人体外化的器官”不同,伊里奇对现代工具的审视十分决绝。他不排斥工具本身,却深感人类正处于尺度失控的边缘。在他的理论中,技术的使用存在一个幽灵般的临界点:一旦越过某个阈值,技术便会从人之延伸异化为人的囚笼,反噬其诞生的初衷。比如医疗系统在履行治愈责任的同时制造出全民性的疾病焦虑;城市交通系统在缩短距离时也制造了无尽的拥堵。伊里奇将这种逻辑称之为“结构性的反生产性”:当工具的巨轮加速转动越过了那处难以预见的阈值后,它制造的问题往往比它解决的更多。
这种逻辑在我们所经历的数字化警告中尤为清晰。这些算法系统本意是为生活锚定安全,但其在修补裂痕的同时,也使人本身对人类直觉生疑和放弃。伊里奇主张划定一道边界,通过拒绝某些越界的技术,来守护人类主权的孤岛。这种姿态在唯技术论盛行的今天或许显得不合时宜,毕竟人们不会愿意拆除现代世界的舞台,他的激进观点也不会像斋藤幸平那样受左翼重视,但也戳破了进步不可逆这一现代神话的幻象。
理解技术困境的生物学路径来自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她是美国进化生物学家,内共生理论的主要提出者之一,该理论已被主流生物学界广泛接受,并被视为阐释真核细胞起源的关键框架之一。马古利斯强调共生、协作与长期嵌入关系在生命演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她笔下,生命的飞跃是一场与陌生者的长期同居。比如真核细胞的起源,本质上就是一次同居后的融合:线粒体是保留着原始野性的共生客。
这一视角瓦解了人与技术的传统二分法。技术不再是人类意志挥舞的锤头,也不再是等待被审判的外部闯入者,它作为人类无形的入世血肉,与人类的关系不是主仆而是同谋。当数字系统嵌入我们的感知与断裂,我们早已与芯片、算法共同呼吸,作为今日的赛博格。
共生视角对海德格尔式技术理论的批判构成了有力回击。我们也无法再像伊里奇那样奢望退回到某个阈值之前,在当下,技术已无可避免地成为我们感官的基底。问题不再是如何重新夺回控制器,这是旧时代的傲慢,而是如何在这一场无法离散的、如同连体婴一般的婚姻中,重新定义责任、脆弱与限度。
第三部分:在技术与反技术之间,我们能做什么?
如果说斯蒂格勒描述的是我们已经身处其中的现实,伊里奇身处拒绝与批判的位置,而马古利斯则指向一种尚未完全成形、却已无法回避的方向。这早已不是选择哪种立场能解决的问题了,我们应该承认:现代社会的技术处境,本身就需要被分层理解。
我们必须正视的,是斯蒂格勒理论的现实意义。技术已然是构成现代生活的基础设施与时间结构。数字系统、风险预判与警告机制,不是可以简单退出的,它已经是维系交通、医疗、能源、通信的条件,维系现代自由是条件。在这一层面上,任何回到前技术状态的想象,都是对现实的误读。
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接受技术对主体的全部定义。斯蒂格勒提醒我们技术药性的危险不在于存在本身,而在于被完全交付给不可协商的系统逻辑。在现实层面,继续的技术路径所能做的,并非卷生卷死地优化系统,而应该对技术介入生活的节奏、密度与解释权提出要求。换言之,是拒绝将技术发出的警告直接内化为对自身价值和能力的判断。
某种程度上,这对人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主体必须在与技术的共生关系中保持清醒的判断力。人不能是被动接受的技术对象,而需要主动划定自己对信息的信任界限,保留身体经验和直觉判断的空间,在使用技术时仍能保留对自身感知、行动与选择做出自主解读的能力,在技术的逻辑与节奏中找到自我立足点。
与此同时,伊里奇的批判作为社会掀掉屋顶的警觉,其地位不可替代。坚持社会有权设定边界、人类有权说不的态度也很重要。但问题在于,拒绝的代价并不能被普遍承受。这个年代,让人们重新回头是岸过“苦”日子怕是也不再可能。也正因此,批判可以持续制造不适感,使技术进步不至于在毫无阻力的情况下自然化。
相较于立场鲜明的反技术,马古利斯的共生视角,或许更符合普通人在现实中与技术纠缠共存的实际处境。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源自一种无法解除的相互嵌入。技术早已进入人的感知结构与判断机制之中,而数字化警告的令人焦虑,也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人理解自身状态的组成部分。隐秘的被侵入和改造的焦虑乃至恐惧也多次出现在各种艺术、影视作品中,持续表达着数字在人类大脑中的扎根,就像我们对Gen-Z Stare的理解一样,数字、技术在每个时代实现着它对人类不同形式的改造。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能做什么”这一问题,本身就需要被重新定位。它应该跳过一切,直接指向人类如何重新理解主体性。如果人与技术已经构成事实上的共生单元,那么主体性就很难再被理解为完全自主、完全掌控、完全透明的存在。它更接近于一种有限的、被延迟的、能够与不确定性共处的状态。人不必将技术系统的评估视为终极裁决,也不必要求自己始终停留在可量化的安全区间之内。为模糊、犹豫和未被计算的经验保留空间,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抵抗方式。
技术必然会愈发实现着其“进步”,但主体并不必完全按照技术发出的警告来理解自身。在技术与反技术之间,公共讨论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提供新的视角帮助人们辨认自己所处的位置,避免将结构性的技术困境误认为个人能力不足,承认共生关系中难以消除的颗粒感。
参考文献
Stiegler, B. (1998).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iegler, B. (2010). Taking Care of Youth and the Generatio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Illich, I. (1973). Tools for Conviviality. Harper & Row.
Margulis, L., & Sagan, D. (1995). Microcosmos: Four Billion Years of Microbial 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iamond, J. (1997).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W. W. Norton & Compa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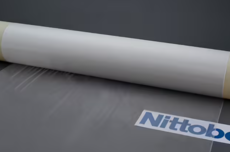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