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康药业曾靠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坐稳高成长席位,但2024年业绩暴跌、费用爆炸、资产减值本应是风光不再,却成了司法拍卖节点股价精准配合的标的。
资产降价、资本异动、制度套利三者一体,悦康正在经历一场与市场、法律共舞的非常规博弈。
据天眼查显示,悦康药业自身风险达62次。
被过度依赖的银杏叶:业绩困局已成常态
悦康药业曾凭借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这一单品爆款,在上市初期享受高增长红利。然而,2024年财报揭示的问题已无从回避:
- 营业收入37.81亿元,同比下降9.9%;
- 净利润仅1.24亿元,同比大降33%;
- 销售费用仍高达5.49亿元,占营收比例近15%;
-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近1亿元,导致扣非利润大幅缩水;
- 所得税费用同比增长近70%,叠加利息支出上涨,令盈利压力雪上加霜。
银杏叶制剂多年来屡遭医保谈判压力与地方控价,一度存在同药双价的争议。悦康也于2024年底主动调低全国中标价格至11.2元/支,以此回应监管。
但问题是:当一个公司超过六成利润倚重单一品类,其定价体系一旦受控,盈利模型就难以为继。
即便公司试图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海外布局等方向寻求增长突破,但实际收入占比仍低,技术管线商业化节奏缓慢。
净资产缩水,现金流紧张,偿债能力存疑
悦康药业的财务结构也正面临高度紧张:
- 截至2024年底,公司账上货币资金约6亿元,金融资产7.8亿元;
- 有息债务却高达6.9亿元,其中长期借款2.6亿元,短期贷款4.3亿元;
- 财报显示年度利息支出已达2240万元;
- 公司年内仍多次公告以持有至到期金融资产质押融资。
这意味着,即便看上去资金尚可,公司仍需依赖资产质押和短期拆借维持流动性。在主营产品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其偿债安全垫明显变薄。
在这样的背景下,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冻结,成为债权人维权的关键。
司法执行遇上市场踩点异动?
2025年5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上线悦康药业2650万股股份拍卖,起拍价为13.73元,几乎等于当日市场价13.75元。尽管拍卖页面显示有91人关注,最终无人出价。
然而,真正的高潮从流拍第二天开始。
5月28日6月23日,悦康股价单边上扬,累计涨幅超过50%。期间成交量迅猛放大,市场开始注意到股价与司法信息披露之间的高度同步:
- 4月27日一拍公告后,股价30日内跌去近20%;
- 5月28日一拍流拍次日,股价快速反弹;
- 6月13日,实控人小幅增持4.74万股,并发布不影响控制权公告;
- 公开信息显示,6月2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计划按市价9折设定二拍底价。
这类踩点式行情引发市场联想是否有资金在关键节点前介入,从而引导预期、干预价格、影响司法定价机制?
如果法院最终以高位九折作为二拍基准,那不仅背离了拍卖流拍→降价→再拍的传统路径,也可能造成后续流拍情况下以物抵债的高估清算,债权人实际收回资产价值严重缩水。
程序拖延半年未裁,估值迁移博弈
2023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裁定悦康实控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债务人虽提出撤裁请求,但经北京市高院终审驳回,裁决正式生效。
然而2024年底,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后,法院又受理债务人重复提交的不予执行申请,并至今未裁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裁决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法院应在两个月内作出裁定,特殊情形最多延长至三个月。而悦康案件目前已超过六个月未裁,债权人权益陷入程序冻结。
一位法律从业者直言:不予执行的理由与早前驳回理由重合,仍被法院受理并长期未决,这在实务中极其罕见,几近变相中止执行。
悦康药业控股股东虽暂未在市场直接大笔减持,但从制度层面分析,这一过程可能形成一种制度内估值迁移的场景:
假设路径如下:
债权人执行 → 首拍流拍 → 股价上涨 → 二拍定价抬高 → 再次流拍 → 转为以物抵债 → 抵债按高位估值执行 → 控股股东部分债务以高估值资产兑付 → 实际偿付压力下降
这是一个典型的间接收益闭环:不通过交易获利,而通过影响市场预期和制度定价逻辑,实现对债务压力的转移和价值的变现。
拍卖流不流拍不重要,关键是它在什么时候被定价、以什么方式转为清偿资产。
在这个模型中,债权人处于相对被动的一方:
如果股价因信息博弈而被短期抬高,而法院又以高位九折作为评估基础,债权人在流拍后面临高估值抵债;
假设市场价格为11元,而法院起拍价设为18元,即便九折抵账,也意味着资产价值虚高,清偿效率下降;
在悦康药业标的接近5亿元的规模中,这种差价清偿可能带来高达两亿的隐性损失。
而反观债务方,即便不通过现金变现,也可能通过这种价值转移降低自身偿付压力,达到缓解资产负担的目的。
从司法制度角度,这种结构并不违法,也未违反拍卖程序,但其合理性与公允性值得重新审视。
以时间换空间的是资本,付代价的却是制度
我们必须追问:司法系统在强制执行环节,是否拥有足够工具应对市场干扰?制度的设计是否已被某些策略性行为提前解构?
司法制度不是市场工具,而是公正机器。一旦起拍价可以被预期操控,一旦程序节奏可以被交易节奏内化,制度的约束力就不再足够。
没有发生交易,并不代表利益没有转移。悦康药业拍卖事件展示的是一种隐藏在程序边缘的估值套利过程。
从银杏叶提取物的独大依赖,到研发转型迟缓;从费用高烧不退,到拍卖节点股价异动;从仲裁胜诉的难以兑现,到程序执行的主动失灵悦康药业这家曾被资本市场热捧的企业,正在以一种更隐蔽但真实的方式,展现出其系统性的问题结构。
问题的核心在于:当企业面对财务危机时,不再首先寻找产品转型与基本面修复,而是通过司法时间差、价格锚点变化、拍卖-估值-抵债的路径,去完成一种合法形式下的价值迁移制度的本义,就已开始被消解。
司法制度,本该是维护契约正义的最后屏障;但当它成为企业压力转嫁的缓冲器,甚至是高估值清偿的通道设计师,那么最终受损的,不仅是债权人,更是整个市场对制度本身的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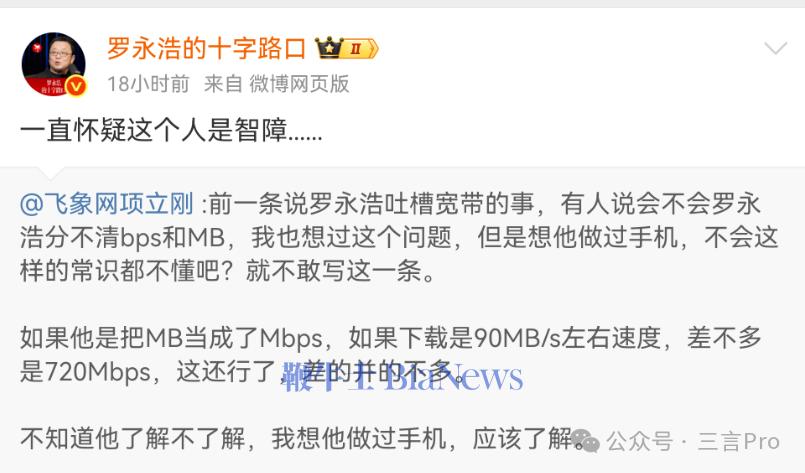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