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脑机接口是一场漫长的战争,充满太多未知。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谭丽平
编辑|张昊
图片来源|受访者
今年上半年,阶梯医疗创始人李雪一直处在快节奏中。
2月,阶梯医疗公布了3.5亿元的B轮融资,由启明创投、奥博资本和礼来亚洲基金等共同领投的这轮融资,被媒体定义为“中国侵入式脑机接口行业历史上最大的一笔”。
3月,一名四肢截肢的受试者在华山医院接受了阶梯医疗的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经过3周的训练,已能“脑控”电脑光标,用意念玩赛车、五子棋等游戏,光标操控水平与普通人控制触摸板相近。
当这一消息在一个多月后对外发布时,包括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官方公众号“上海科技”在内的众多媒体,在标题和稿件里直接用到“追赶马斯克”“中国创新方案”等表述。
李雪预料到了这个状态,此前她在内部还专门讨论过这件事——是不是要去对标马斯克拥有的脑机接口赛道明星公司Neuralink。
虽然,她在2021年成立这家公司时,定的愿景是“世界的阶梯”,而不是“中国的Neuralink”,但这是个太新的事,连她自己都承认,正是马斯克的出现,让脑机接口本来该在2030年才实现的目标,提前了近10年就出现了。

对于很多“圈外人”来说,提马斯克显然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而且不得不说,这个原本“小众”的前沿技术赛道,在全球科技战的特殊时间段内,一下子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上半年,脑机接口被资本市场热炒。香港公司脑再生科技只有12名员工,股价半年涨超460倍,以至于媒体惊呼:脑机凶猛。
5月初,阶梯医疗组织了一场媒体沟通会,记者的很多问题直指与Neuralink的竞争优劣势。
也就过了一个月,Neuralink就宣布了一轮6.5亿美元的融资,估值已突破百亿美元。紧接着在7月,它单日成功完成两台手术,这是行业的首次。
李雪还在努力保持着自己的方向和节奏,因为这是个连技术路径都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的赛道,有太多不可控性。在她看来,乃至10年之内,阶梯医疗的核心工作都是推动更多产品管线进入临床阶段,以及商业化。只有产品落地,才能证明她的判断。
就这样,一到两年落地一轮融资,随着市场变化,“钱多了,就拆更多的管线出来”。在她的描述中,阶梯医疗第一阶段的三个重点领域都是超级大市场:第一个是脑控,用外部设备帮助瘫痪、渐冻症患者做运动功能替代;第二个是精神类系统性疾病的调控,用“电子处方”解决当下没有技术手段的问题;第三个是感知觉恢复,这是针对失明、失聪人群。
“这些都是很直观的疾病,一直在往后推,至于到底先推哪一条,中间是不是要加速或者放缓,我们确实会有调整变化。”李雪说,“但大方向可以说在10年前就确定了。”
“倒金字塔”
李雪很早就开始规划自己的“终极职业”。
她说自己想问题的方式“偏简单”,上大学前就琢磨人和猴子的区别有两个:一个是用火,一个是说话。这对应的是两个行业,“用火”是能源,这本是她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高能核物理,结果没被录取。
她因此走上了第二条路——说话。“我在这说一个小时的信息量,如果转成信息发送出去,可能就2秒,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把数据传输量给提升上去,包括把学习能力给提升上去?”她选择了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开始有意识地研究大脑。
2016年,她赴美深造,又分别于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莱斯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学院,完成了硕士及博士学位。
实际上,在去美国之前,她已经很明确自己未来要从事脑机接口的工作了。而且,她对于这件事的拆解已经有了雏形。
现在,她习惯用“倒金字塔”结构来说明对脑机接口的理解。
“最下边一层是神经界面,如何有效、稳定地把大脑的信号提取出来去控制外部的设备,这是脑机接口里最核心的部分。因为要长期使用,需要它不产生免疫反应,和生物体的交互是非常难的。再往上一层是系统,只有一个被动的器件是不够的,需要一个主动的系统去做后面一系列的工作,比如信号放大、数字化压缩传输等。第三层是临床,要把系统真正地放到临床上去,拿到更多的数据和反馈,知道它有什么问题,要往哪方面做改进。最上边一层是神经科学对大脑的理解程度,这是天花板,想解决一个疾病,肯定是看对这个疾病的理解程度够不够。”

她此后的学业完全基于这个结构展开。本科学的是生物医学工程,她最熟悉的就是“神经界面”层,到了美国之后,研究生阶段学习了计算机,补强了对“系统”的理解。2020年回国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她领导的多模式神经界面研究组,就是在发掘开拓一些脑机接口技术在临床治疗上的价值。
2021年8月,她就成立了阶梯医疗。“我强烈意识到做研究和商业的区别。做研究的目标是颠覆式创新,而是否可以量产,是否容易获得?并不是大家优先思考的点。”但李雪是“产品主义者”,“如果要把这件事情推到临床上面,我们最关心的其实是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李雪并没有过多的纠结,因为在她的理解中,脑机接口未来更大的价值体现是在消费端,那更需要靠产品去驱动。
团队把公司名定为“阶梯医疗”,这看上去跟她的愿景有差异,但她那时很冷静,因为确定的技术路线是“侵入式”,那时市面上更多的是“非侵入式”。侵入式牵扯到有创,产品和审批的复杂度要大得多,但因为采集的数据量庞大,对应着巨大的商业价值。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消费级市场,但中间的阶段一定得以医疗为场景去做。因为我们做的是侵入式,不可能一下子就用到正常人身上。”李雪一开始只是组了一个小团队,更接近于工作小组的形态。
那时,她还没有去规划发展路径。阶梯医疗的第一轮融资也特别简单,李雪只见了一个投资人,用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2021年整个融资环境还比较好,天使投资人比较友善,更多是投人,给我们的资金和估值锚定都不错。”那个阶段有其特殊性,还没有太多投资机构知道如何判断一个脑机接口团队是否优秀,但开局顺利,给李雪增加了很多信心。
“漫长”的10年
按照她的“倒金字塔”结构,阶梯医疗这几年最核心的工作就是中间两层。神经界面是李雪的老本行,上学阶段,用神经电极在实验动物脑子上做实验就是日常内容。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尖尖的电极进入到脑组织里面,就像是把一个小钉板插到豆腐里面,还得再晃一下,中间会有比较严重的损伤和免疫反应。”李雪需要实现让大脑意识不到被插入一个异物,“电极的前端是可以在空中飘起来,纤细到直径大概是头发丝的1%,这才能让你在弯曲电极时用的作用力,跟两个细胞之间的互相作用力差不多。”

这在她的能力范围之内,她更多的工作是要把外部的那个连接设备做出来。
刚拿到融资时,她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面试,即便到了现在,她还是每周五到十场的面试节奏。
脑机接口牵扯到很多模块,在中国创业的好处是单拎出来一个模块,都有充足的人才储备。“但难点是得找到哪些人适合做哪些部分,并且拉他们进来,得让他们知道这是件什么事情。”李雪跟团队密集地沟通产品需求和技术需求,板子怎么设计,边界什么样式……都是很细碎的问题。
2022年时,团队就做出了第一代原型机,不过外壳还是塑料的。
李雪要的是“让正常人都愿意用它”,这意味着产品要做得很小,甚至要好看。很多现在看上去有颠覆式感觉的创新,都源自于团队不断的试错。
“就像我们做结构的同事之前是做耳机的,完全不搭的领域。但仔细琢磨,这个系统部件的核心需求是小、好散热,这跟耳机的需求是很类似的。”李雪试着招了一个有相关经验的员工,果真做得很好,“他可以把里面的结构做得非常精巧,但脑机接口之前很多从业者都是传统医疗器械出身,并不太在意这一点,做大点就大点,反正都能装进去。”
就这样,团队在系统上磨了几年,产品迭代了好几版。
李雪还在牵头一个重要工作——临床。主要目标就是检验系统是否能够有效记录、稳定性如何等。
当时,他们做了50多例患者。“真正去记录人类大脑的神经元对于一些事件的反应和变化,比如说话、听音乐等。”李雪要在保证系统安全性的前提下,大规模地尝试各种数据采集的方式,“电极上有位点,尺寸、排列方式都有讲究,要在实验过程当中去看到底哪一种结构和排布是更好的。”
2022年,李雪就跟B轮融资领投方启明创投聊过,之后就没有后续了。等到2024年再一次见面时,打动启明创投的一个核心点是,彼时提到的几个关键节点,团队全兑现了。
面对着一个注定很“漫长”的战争,李雪把阶梯医疗的核心竞争力定位到了人才上。
2024年,李雪面临很大的融资压力,尤其是研发人员很多,对应着更高的成本。有很多人劝她,要不先裁掉一些,边走边看。她很认真地反思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给我这些建议,这是不是合理的建议?”李雪自信于团队氛围,甚至跟同事有过交流,竟然有人支持这件事。
“尤其是传统医疗器械行业。很多研发人员从一家企业离职,都是因为没事干,没新管线和产品了。但脑机不一样,我的核心竞争力其实不只是一款产品,是一系列的东西,要不断去迭代和提升。”
那如何去跨越这个“10年”?李雪觉得只有靠团队,一起走过去,“其他的钱都可以往下压一压,但是关于人员的投入,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这个行业太新了,有大量工作要做,也充满了太多的未知性。“我们其实是在给整个行业蹚路,做了比较多目前没有的检验检测标准。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持续保持身位,能够持续得快一步,真正在这个市场上去证明我们的一些竞争力。”李雪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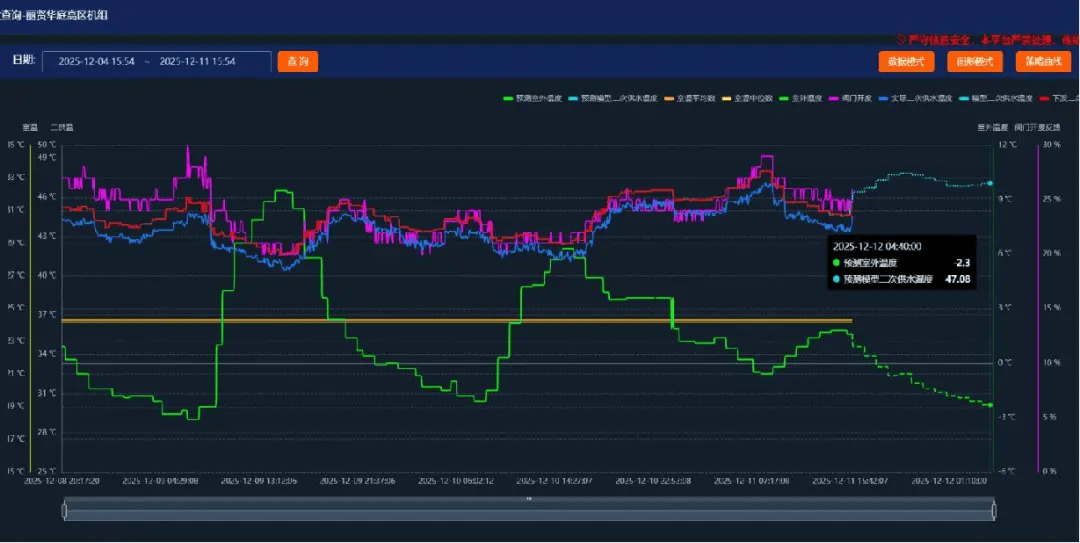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