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的一骑绝尘中,中国大学迎来2025。
2025年,注定要成为变革的年份。是以战略敏捷赢得战略主动,还是在延误中错失转型机遇,中国大学踏上征途。
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赋能学科建设?人工智能技术给创新人才培养带来哪些启示?澎湃新闻特推出“大学2025”专题,以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学之变。
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润生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是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的,科学智能需要成为善意的智能。科学需要传承,传承需要教育,所以科学本身的发展有赖于科学教育。如果一个科学家能够肩负起教育家的责任,当然是很好的,但毕竟科学家和教育家是不同的,科学家应当在教育这个领域探索和努力,才能够肩负起教育家的责任。
“早在1988年,我就用复杂神经网络,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人工智能做研究工作。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不叫人工智能,但是也早已经把这个方法用来解析基因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润生是中国最早从事理论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和非编码RNA研究的科研人员之一。
生物信息学是以生物学、数学和信息科学为基础的交叉科学,通过综合运用数学和信息科学等多领域的方法和工具对生物信息进行获取、加工、存储、分析和解释,来阐明大量生物数据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研究重点主要是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直逼人类基因深处的秘密。
三十多年来,陈润生在生物信息学领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曾参加中国第一个完整基因组泉生热袍菌B4基因组序列的组装和基因标识,以及人类基因组1%和水稻基因组工作草图的研究。他构建了收录非编码RNA及其基因的数据库NONCODE,以及收录非编码RNA与其它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的数据库NPInter,这两个数据库已成为国际在非编码RNA领域非常有影响力的数据库。
此外,陈润生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开设生物信息学课程的人。1988年,该课程首次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前身)开设,当时这门课程在国内外都处于摸索阶段,课程内使用的所有算法、程序、理论都是陈润生自己推导的。目前生物信息学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科核心课,同时也广泛吸引了来自医学、化学、材料、环境、计算机等学科专业的学生选修。如今,80多岁的陈润生仍然在国科大的讲台上为同学们讲课。
近日,陈润生院士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强调,科学发展永远是交叉融合的。新的学科不断出现,这是一个科学发展的必然。因此,陈润生鼓励年轻人不断探索未来,不断去关注学科交叉融合,“年轻人要多去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或别人没有想过的事情,这样社会才能更加活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润生。 国科大供图
以下是陈润生院士与澎湃新闻的对话:
澎湃新闻:您是内地第一位教授生物信息学课程的教师,教材也是您自己原创的。当时您是如何设计的课程体系?在这种“无先例可循”的学科建设上,有哪些经验分享?
陈润生:第一次把生物信息学作为一门课程是在1988年。之所以开设这门课,跟我在国外和在国内的经历有关。在国内,我参加了唐敖庆先生的量子生物学讲习班;在国外,我做的是生物大分子的电子结构和空间结构的理论研究。所以,我先把这两部分内容融合起来,作为理论生物学的一门课程,讲给第一批学生听,那个时候的学生大约有30个人。
两年之后,人类基因组的概念在科技界被大家逐渐关注,那时我也在为自己未来的科研选择方向和重点。当时我认为破译人类遗传密码一定是未来重要的科学事件,所以我把讲课内容逐渐从理论生物学过渡到生物信息学。后来就在生物信息学这个轨道上,不断地更改、更新自己的教学内容。
生物信息学第一个阶段是遗传密码的破译,也叫测序基因组时代的生物信息学。后来,我们有了生物芯片和功能基因组,第二部分的内容就升华到功能基因组阶段,再后来,有了系统生物学,就把生物信息学增加了系统生物学内容。整个课程的演化完全紧跟国际上该领域的发展,不断地更新。我想这也是学生们乐意学这门课的原因,能够使得他们紧跟这个时代发展,使得他们站在国际这个领域发展的前沿。
澎湃新闻:您研究的生物信息学包含着对基因组信息的获取、处理、加工、分布、分析和解释,通过挖掘生物大数据来分析深刻的生物学内涵。如今生物信息学与AI大模型发展迅速,您认为它们将如何改变生命科学研究范式?
陈润生:我在1992年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时是负责理论分析的,在理论分析过程中会用到各种各样的工具,早在1988年我就用复杂神经网络,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人工智能做研究工作。
在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前,我们公开发表的论文有一些就是用复杂神经网络或者机器学习的办法研究这个大分子的特征,所以在1992年我参加人类基因组以后,自然地就把这个方法用到了生物信息学研究当中。
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不叫人工智能,但是也早已经把人工智能这个方法用来解析基因组。例如发现基因组当中哪些地方是基因,也用到了人工智能的方法。现在有了大模型,使得对基因和整个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工具。因为大模型提供了大语言模型,把人类的所有知识都集成起来了,也使得整个生物信息学作为一门学科上了一个台阶,有了更好的技术基础。
澎湃新闻:早期生物信息学研究面临“数据少、算力弱”的困境,如今算力与数据已不再是主要矛盾,您认为当前生物信息领域发展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陈润生:在信息领域,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人工智能本身是希望用数字技术来完成或是实现人脑的智能。这是人类从来没有的新的事物,这个新的事物会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工作、研究、生活的范式,这在人类的历史上是重大事件。
而挑战的核心科学哲学问题就是,数字智能能否超过人类智能或者脑的智能,这两个智能体将如何协同?
“AI教父”辛顿在他的报告里讲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等于我们培养了一只老虎崽,它长成老虎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那长成老虎就可能吃你怎么办?这就是培养了一个人工智能面临的问题。这只老虎可能你用好了对人很有用,它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它有自己的诉求,有自己的智能,但是它也可能起坏的作用。所以辛顿认为,人工智能将来要并行发展为两类,一类是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另外一类要培养未来的数字智能,让它形成一个善意的智能,而不要成为破坏人类的智能。
澎湃新闻:您曾指出,对比发达国家,我国在基础研究阶段已有赶超趋势,但临床转化的道路“道阻且长”。不断涌现的基础科研成果,并没有在成果端得到效率体现。您认为应如何提升临床转化能力?
陈润生:我们知道整个生物医学的研究,实际上终极的目的是改善人类生活,提高人类健康的素质。医院是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因此它也是获得各种各样健康信息的第一场所。所以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在健康领域的发展其实跟医院是有紧密的相互作用的。
我们知道一个人工智能是三个要素组成的,一个要素就是算力,这个是由芯片发展。第二个就是模型,就是怎么来建造一个物理的系统,能够来变成一个信息加工的场所。第三个就是所谓数据,医学的数据很多是来自临床,所以临床数据的收集整理是发展专业大模型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所以如何把数据收集起来,如何把这些数据标准化,让这些数据能够不仅仅是一个医院,而是把各个医院的数据都整合起来。这是未来做好生物医药大模型的关键性步骤。
澎湃新闻:您认为目前关于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的这个交叉领域,还有哪些地方是空白的?您觉得哪些领域值得科研人员继续探索?
陈润生:人工智能可以说是一个平台,是个范式,每一个领域都应当为自己这个领域建一个专属于它的模型。有很多的垂直模型还没有建设,所以总体来讲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
我认为人工智能本身也还在发展,很多人工智能的专家认为人工智能目前只有5岁到10岁的年纪,很多的人工智能的理论还在不断发展。有一些著名的科学家质疑现在用的大模型的这套理论体系是能够长久地保存吗?有人讲只有几年时间,过了几年它就被推翻了,会有新的智能模型出现,从各个垂直模型到总体的人工智能系统理论的发展,有太多值得斟酌和考虑的空间。
此外,科学发展永远是交叉融合的。新的学科不断出现,这是一个历史科学发展的必然。因此我鼓励年轻人不断探索未来,不断去关注学科交叉融合。
我希望年轻人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或别人没有想过的事情。年轻人应当更勇于为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去探索一些有利于社会的,但是别人没有做过没有想过的事,这样社会才能更加活跃,更加积极。
而科学本身是要传承的,传承是需要教育的,所以科学本身的发展有赖于科学教育。如果一个科学家能够肩负起这个教育家的责任,当然是很好的,但毕竟科学家和教育家是不同的,科学家要成为教育家的话,应当在教育这个领域探索和努力,才能够肩负起教育家的责任。科学家要变成教育家,这是科学发展的需求。科学能够传承,能够使得我们不断地培养年轻人,这是一个系统的延续性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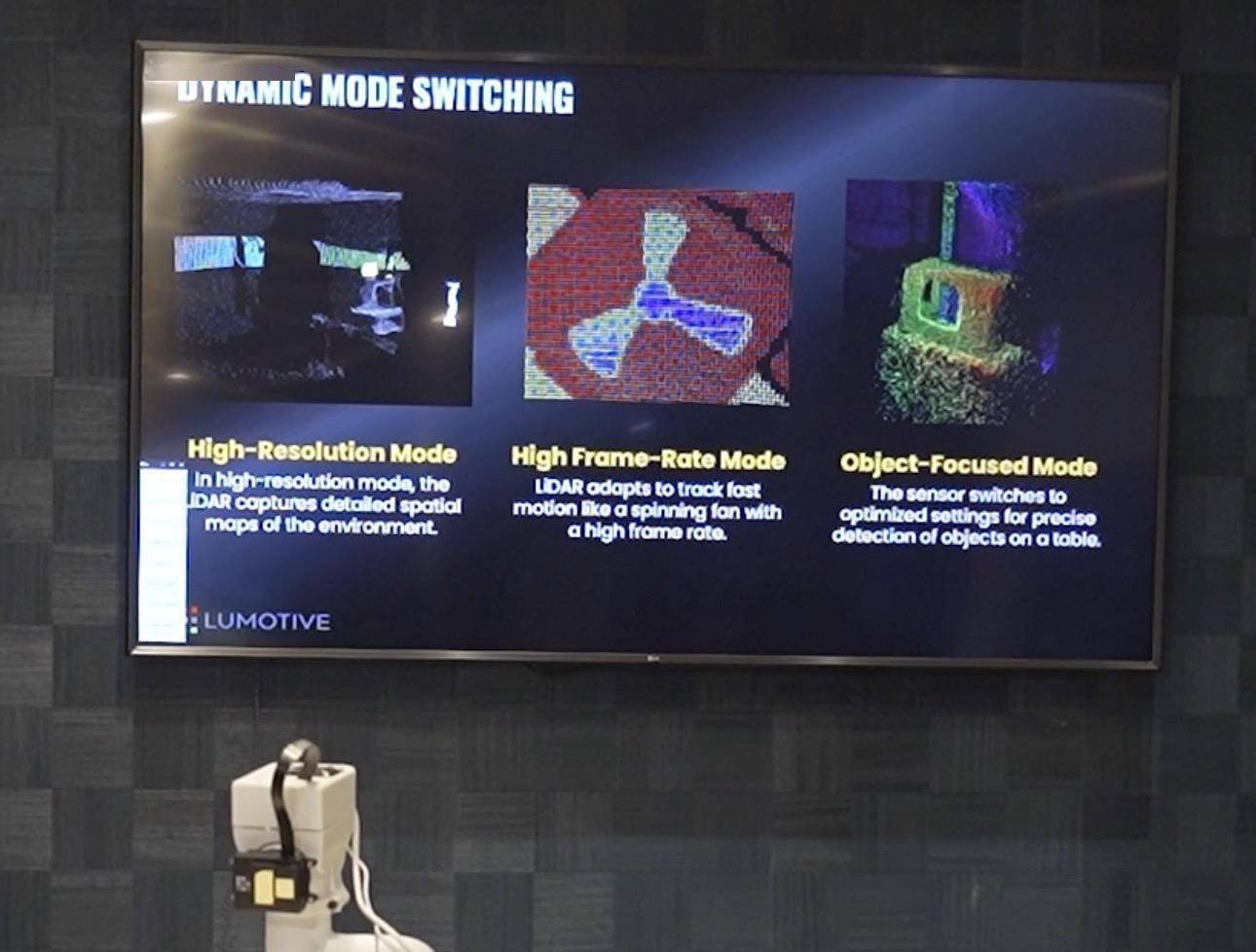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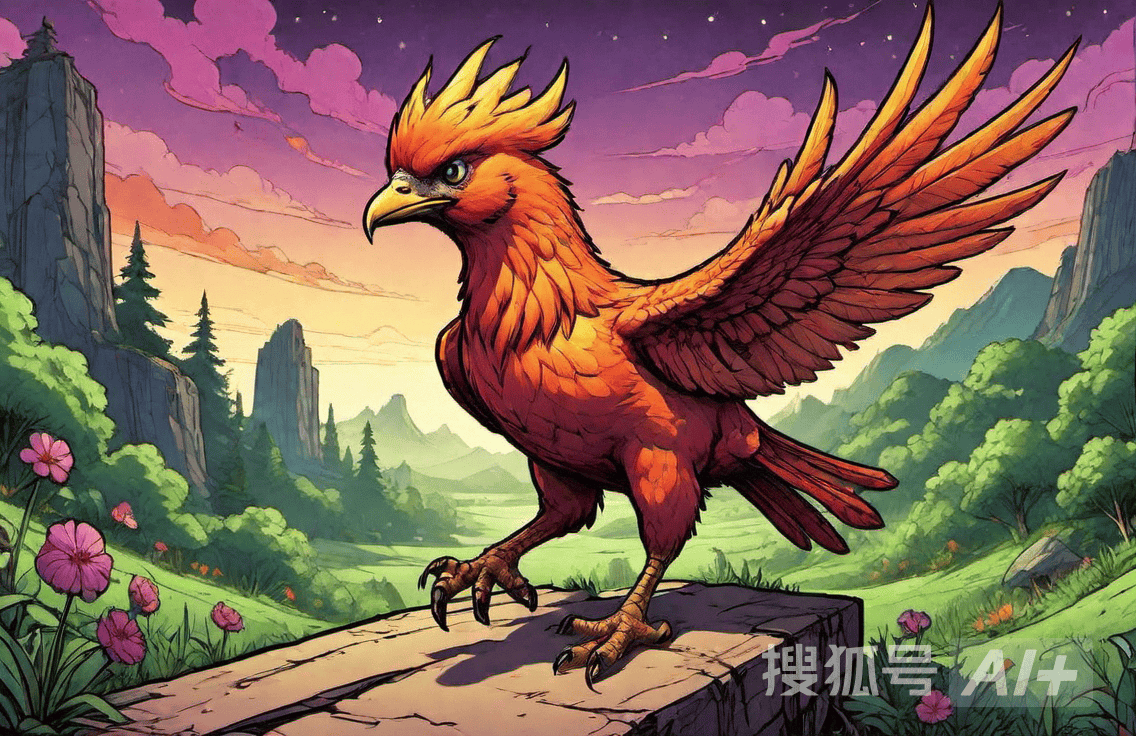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