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用人工智能(AI)写作业,老师用AI改作业,最终比拼谁的AI更好用、更先进?这看似是笑话,但事实上,自从AI大模型诞生以来,如何辨别学生论文的AI生成率一直是一个难题。有机构统计,美国超过一半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都用过生成式AI来完成作业或考试。
据媒体报道,以GPTZero为代表的一批检测工具正快速崛起,它们不再只是简单地给出“AI生成概率”,而是能精准识别文本的生成轨迹。各个检测工具、平台等也都加大了对AI论文的检测强度。
生成式AI正把我们推到一条更陡峭也更开阔的教育变革之路上。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而言,要变革的不仅仅是教与学的方式,更是整个教育的思想。
师生间的“攻防升级”并未终结
在教师与学生围绕教学展开的“拉锯战”中,AI与人类教师正推动一场持续迭代的“攻防升级”,这甚至被称为师生之间的“AI军备竞赛”。
在学生侧,AI正从“直接生成”进化为“多步加工”:先用来检索教材与权威来源,再用提示工程诱导组织推理,随后通过个性语料调整与词频、句法、标点和元数据的细微扰动,以及AI模型二次内容改写,来弱化“AI痕迹”。
在教师侧,可检测从单一“AI率”走向“证据拼图”,教师也可以利用AI,综合困惑度、句法树多样性、指代稳定性、引用可检索性、提交—修改时序与键击编辑轨迹等多模态信号,了解作业的AI含量,同时在作业中引入相似度图谱、在论文中用检索技术复核与溯源。
甚至,更进一步,教师在教学上将转向“过程导向”的教学设计,不少教师会要求学生提交思维链、草稿版本与口头复述,把AI纳入“生成—校验—反思”的可控流程,让“代写”逐步转化为“助学”。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平台曾尝试提供的“灰色服务”,即提供一些“人类化工具”的人工智能,也很难再进行下去。
不禁止学生使用AI,但要对使用负责
当学生可以用AI完成本应自己思考的任务时,当AI既能出题又能解题时,传统的客观题、编程题乃至论文写作,就学生的学习成果展开评价时,区分度会被削弱。
不过,我们不应把这简单归因为“作弊工具的升级”,更应该接受这是一场关于“解题权”的结构性再分配:在答案易得的时代,学习的价值不再是写出正确答案,而是如何理解问题、如何形成思路、如何组织证据、如何在协作中迭代。
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对于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评价仍然是结果导向,那么教师和学生之间的AI博弈会迅速演化为“谁调用得更快”。只有当我们把评价转向过程性与场景化,要求在真实或拟真情境中进行解释、复盘与现场取舍,才能区分“会用AI”和“真理解”。
这意味着,未来的教学过程中,将有更多开放型任务、项目式作业、口头答辩与在场评测,意味着提交作业时要附带“AI介入说明”和“版本迭代记录”,意味着会把“证据链”与“可解释性”纳入评分的硬指标。在这样的框架下,学生不被禁止使用AI,但要对其使用负责任:学生必须说明调用点,呈现比较与取舍,展示失败与修正,接受当场追问。教与学的透明化过程证据,会重新建立学习的公正与可信。
好老师的“隐性价值”将更显眼
事实上,在不少学校,AI正在重组教育供给。
对学生而言,AI只能成为学习的辅助工具;同样,对教师而言,AI也只能是“副驾”,AI可以接手规模化、可标准化的创作任务,让教师把时间花在更有专业价值的地方。比如,搭建课程蓝图,规划能力坡度与台阶;精选关键案例与“高错点”,针对性地拆解误区;组织讨论、共创与辩论,引导价值判断与伦理思考;在质量管控上设立标准、抽检样本、校审输出,用数据驱动版本的持续迭代。教师的这种转型,本质上是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向学习的架构师与引导者。
而过去无法规模化复制的好老师的“隐性价值”,包括教师的专业判断与人文关怀则被放到更显眼的位置。以上海交大人工智能学院教师智能体“TeachMaster”为例,它承担内容生产与流程编排。在高效的人机协同下,教师仅需提交文字版课程大纲以明确教学目标与内容边界,系统即可在数小时内生成整堂课的教学视频与配套课件;在备课阶段,教师通过预览环节进行标准与质量校验,重点防止知识幻觉与事实偏差;实际课堂采用“AI主教+教师助教”,教师则专注现场答疑、个性化辅导、拓展讨论与价值观引导,并对学习数据进行二次解读与纠偏。由此,教师从繁琐的备课与课件制作中大幅解放,职责上移至目标设定、内容边界与质量把关等高阶决策层,重复性制作与编排工作交由AI完成。
以人机协同重构“传道、授业、解惑”
虽然AI在教与学中的推广使用,可以使得优质教育资源得以更广泛地被普及,但是,生成式AI在教与学的落地过程中,仍有四道难关:
其一是知识粒度缺口。现在大多数通用模型的强项是广度而非细度,高阶专业教学引入AI工具,需要通过领域知识库、专家标注与小样本微调来补齐,并建立“错误本体”与“误区图谱”,让系统对“细小但关键的差异”保持敏感。
其二是评测体系危机。当AI实现“秒解”,标准化测试的效度下降,我们就需要把口头解释、开卷在场、限定资源与可追溯证据链作为教与学的测评中的新常态,通过推动“过程的真实”来实现“结果的可信”。
其三是政策与治理尚未完善。数据隐私、版权归属、责任界定都需要明确的制度护栏,校园内应建立可信模型白名单、分级授权与日志审计,把可验证、可追溯落到流程。
其四是算法厌恶与组织惰性。很多时候,机构或者公众抵触的往往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价值、制度与场域的综合反应。
在快速演进的AI时代,教育应以人机协同重构“传道、授业、解惑”的分工:“传道”意味着教师把握价值取向与学术规范,并将其编码为可执行的系统规则;“授业”意味着AI实现个性化、标准化、规模化的传授,教师专注于课程设计与难点突破;“解惑”意味着AI进行前置分流、提供证据与路径建议,教师做最终裁决、给予情感支持并引导元认知。
技术并不会让教育“去人化”,恰恰相反,它让人的工作更回到人本身——判断、同理、鼓励以及对价值的坚守。
当前,中国正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当理念和技术同频、供给与评价并进、教师与AI协作成型,教育供给将实现跃迁。优质资源会从稀缺品变为可复制、可规模、可迭代的公共品,教师智慧也被放大为普惠供给,让孩子们在可达半径内都能遇见“好课”“好老师”。当优质供给可被复制与升级,稀缺焦虑自然缓解,“内卷”也将在充分与公平中退潮。以技术作桨、质量作帆、公平作航向,今日起航,驶向教育强国。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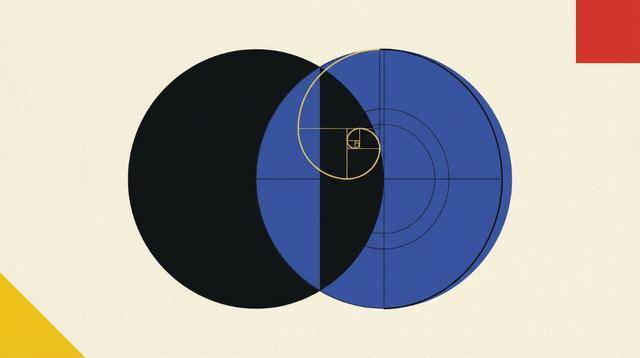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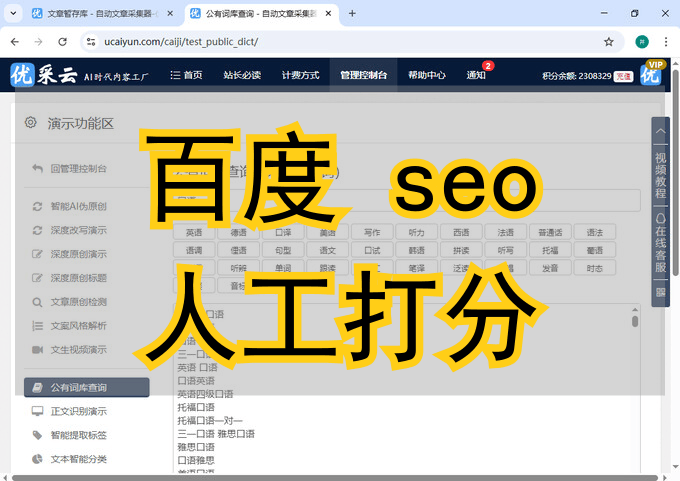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