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at New Hit Song on Spotify? It Was Made by A.I.
怀揣梦想的音乐人正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批量创作歌曲,部分作品还登上了排行榜榜首。

作者:凯尔查伊卡
2025年11月12日
尼克阿特(Nick Arter)现年35岁,居住在华盛顿特区,他从未通过传统方式真正成为一名职业音乐人。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长大,家中充满音乐氛围。父亲和继父痴迷于90年代的嘻哈音乐——比如Jay-Z、Biggie、Nas,几位叔叔则是职业唱片骑师,专门播放70年代的节奏蓝调。青春期时,他和表兄弟们开始录制自己的嘻哈曲目,起初用卡带录音机,后来换成台式电脑,模仿当时走红的少年说唱歌手Lil Romeo和Lil Bow Wow。大学期间(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始终是他的爱好。毕业后,他曾短暂尝试职业化,在当地演出中售卖混音带,之后在哈里斯堡的一家政府呼叫中心任职。这份工作最终让他获得了华盛顿特区德勤公司的职位,而阿特仍会在夜晚和周末继续说唱创作,却从未发行过任何作品。“作为说唱歌手,我年纪已经有点大了,”他最近回忆道。直到去年年底,他开始使用人工智能创作歌曲,短短几个月内,他的作品就在流媒体平台上成为热门,播放量达数十万次。或许他的音乐生涯终究还是到来了。
阿特的成功象征着人工智能正加速进军音乐行业。如今,没有任何文化或娱乐领域能免受人工智能影响:可口可乐刚推出了一部采用人工智能视觉效果的圣诞广告;好莱坞也在大肆宣传人工智能演员。但这项技术对歌曲创作的影响尤为迅速。几年前,少数人工智能歌曲因模仿Jay-Z和Drake等流行歌手的嗓音等技巧而走红。如今,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音乐的全面爆发期。本月,一首名为《Walk My Walk》的人工智能乡村歌曲(带有打击乐般的拍手声和“不喜欢我的说话方式就滚开”这类平淡无奇的歌词)登上了公告牌乡村数字歌曲销量榜榜首,在Spotify上的播放量突破300万次;这首歌的表演者是一个名叫“布雷金拉斯特”的方下巴数字虚拟形象。9月,密西西比州一位年轻诗人创造的人工智能节奏蓝调歌手克桑妮娅莫内,在多首歌曲登上公告牌排行榜后,签下了一份数百万美元的唱片合约。今年早些时候,一支名为“丝绒黄昏”的神秘迷幻乐队在Spotify上的播放量突破100万次后,创作者才承认这支乐队是“合成的”。Spotify并未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标注,该公司表示正在改进人工智能过滤系统,但并未明确界定何为人工智能歌曲。过去一年,该平台已从其服务中移除了超过7500万首“垃圾曲目”,但仍有无数未标注的人工智能歌曲存在,而且许多听众无法分辨其中差异。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参与者成功区分人工智能生成音乐与人类创作音乐的概率仅为53%。
如果你在网上听到一首人工智能生成的歌曲,它很可能是用两款热门音乐创作应用中的一款制作的——Suno或Udio。阿特的创作过程会同时用到这两款应用。他通常在手机上写下自己的歌词,然后结合歌词和对设想中歌曲的备注拟定文本提示词,将提示词输入两款应用,对比哪款能产生更好的效果。(阿特告诉我,“一个好的提示词应包含(年份)、(音乐类型)、(乐器配置)、(曲风)和(情感)。”)他会通过这种方式为每首歌生成几十个版本,反复调整旋律和乐器配置,直到满意为止。最后,他使用Midjourney为每首新单曲创作专辑封面——通常是普通灵魂乐歌手的特写肖像,再将歌曲上传到YouTube和Spotify等流媒体平台。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挣脱那些破事》在Spotify上的播放量接近90万次,这首歌融合了70年代末节奏蓝调抒情曲的风格与嘻哈式的抒情励志元素:“今年我状态正佳/那些阻碍我成长的破事都见鬼去吧。”这些应用允许阿特保存风格快捷操作面板,方便他日后快速创作类似风格的曲目。“算法会 kind of 摸清你的喜好,”他解释道。阿特以“Nick Hustles”为艺名发行的音乐绝非含蓄之作(另一首歌名为《Stop Bitching》:“没人能靠/像个小屁孩一样抱怨变富”),其乐器伴奏和人声中都带有人工智能音效特有的空洞单薄感。但旋律——以及某些抒情亮点,比如《Dopest MotherFucker Alive》中醒目的脏话——足够抓耳,让人过目不忘。
这项技术“开辟了新的创作可能性领域,”阿特说。他从未是一名技艺娴熟的歌手,如今却能涉足自己从小听到大的老式节奏蓝调。突然之间,他可以塑造永恒的虚拟形象来代表自己的音乐,配上虚构的背景故事,而非展现自己日渐老去的千禧一代形象。仅在过去一年里,阿特就创作了约140首歌曲,他并不隐瞒自己的音乐是由人工智能制作的,不过不知情的听众可能不会注意到他的YouTube账号名“为文化而生的人工智能”。他的许多歌曲都像是关于日常生活的俏皮吐槽:“唱的都是堵车、奇波雷快餐弄错订单这类事,”阿特说。他的作品包括《全食超市里的健康女孩们》《我要去睡觉了》,以及《我得戒烟了》和《我他妈又把电子烟弄丢了》,这些歌曲迎合了他所在的受众群体,涵盖了成瘾的各个阶段。他从未为自己的人工智能音乐做过任何营销或推广,但口碑传播和算法推荐(比如Spotify的电台功能)将他的作品推向了他少年时说唱梦想中的流行高度。贾斯汀比伯曾用阿特的歌曲为Instagram帖子配乐,50美分则发布过一段自己在车里跟着尼克哈斯特尔斯的歌曲哼唱的视频。说唱歌手扬萨格借鉴了阿特歌曲《我的兄弟们都很顶》中的副歌部分,用于自己的热门曲目《想念我的兄弟》,并将阿特列为词作者。阿特得以辞去咨询行业的工作,开启了全职“半自动化音乐人”的职业生涯。他现在与音乐发行商UnitedMasters合作,从50多个不同的流媒体平台获得收入。此外,他还为客户的生日或婚礼创作定制歌曲,每首收费500美元(若客户提供歌词则半价)。阿特坚信自己所做的只是一种新的艺术创作方式:如果你的音乐“能改变某人的生活,”他说,“它是否由人工智能创作真的重要吗?”
尽管人工智能音乐广受欢迎,但以大多数标准衡量,人工智能并非优秀的歌曲创作者。正如伦敦音乐人兼制作人艾哈迈德科尔多法尼(他也使用人工智能创作)所说:“人工智能作品中存在一种刻板感,一种深层次的空洞。”科尔多法尼注意到许多人工智能生成歌曲都有一个奇怪的共性——平淡乏味:它们单调且缺乏结构,没有清晰的副歌、旋律走向或高潮部分。“有时候人工智能分不清桥段和副歌,”科尔多法尼说。他补充道,作为听众,他在人工智能音乐中找不到那种“被触动”的感觉。正是看到了这项技术的短板中蕴含的机遇,科尔多法尼开拓了一份蓬勃发展的事业:帮助怀揣梦想的音乐人“人性化”他们用Suno、Udio等应用制作的歌曲。雷萨巴赫是他的客户之一,这位蒙特利尔摄影师创作拉丁风格的说唱和舞曲。萨巴赫先生成歌曲(有时会使用人工智能创作的歌词),然后使用科尔多法尼根据他本人真实录音训练出的人工智能声线模型进行演唱。(萨巴赫说,朋友们听到这个“虚拟的他”时,根本分辨不出差别,还补充道:“有时候这真的很吓人。”)如果人工智能声线在某些地方出现瑕疵,科尔多法尼就会插入萨巴赫本人的真实录音——这个过程虽然繁琐,但仍比从头录制更快。最终的作品悦耳动听,比阿特或布雷金拉斯特的歌曲更具人情味,不过受欢迎程度也低得多。
Spotify的听众是否在意他们听的音乐是否“人性化”?随着人工智能的主流化,合格质量的歌曲可以被即时、无限地生成;这种无摩擦的大规模生产,再加上通过算法推送进行传播,意味着人工智能生成的音乐与网上其他类型的社交内容并无太大区别。音乐的质量或持久性次要于其短暂的冲击力;核心目标是实现“听觉吸引力”。这些音乐可能过目即忘,但如果听众只播放一次——而且他们很可能只会播放一次,因为除了新鲜感之外,这些音乐没有太多深度——而创作者又能立刻再批量产出十首歌曲,那也就无关紧要了。对于怀揣梦想的音乐人来说,这个新生态系统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民主化机遇。“我认为人工智能确实有机会打破行业壁垒,”阿特说。在他的歌曲成为流媒体热门之前,唱片公司根本不关注他;如今他表示自己收到了不少合作邀约,但会观望一段时间,直到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未来更加明朗。他承认,考虑到Spotify上充斥着大量垃圾歌曲,行业准入门槛可能过低——用户试图查找某首普通爵士乐背后的音乐人时,往往只会发现一个匿名虚拟形象,名下有数十张同年发行的器乐专辑,这让用户感到困惑。阿特说,那些音乐垃圾制造者“不重视创作本身”;他们的作品背后没有歌词、没有人物形象、没有明确的创作意图。他认为自己对人工智能的运用远高于这些行为。“我不会做那种工作,”他补充道,“我太爱音乐了。”♦
本文作者:凯尔查伊卡是《纽约客》的专栏作家。他的专栏“无限滚动”探讨了塑造互联网的人物和平台。他的著作包括《过滤世界:算法如何扁平化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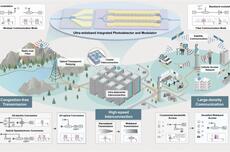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