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缘政治持续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欧美市场的国家安全审查,到欧盟碳关税、ESG立法等新型壁垒,再到国际供应链的重构与合规政策不断升级,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对中企的全球化战略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日,富而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庆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中企出海面临更多障碍,但相关行业数据仍显示,中国对外投资总额2023年超过1300亿美元,2024年达到1400多亿美元,2025年仅前4个月便达到500亿美元,2025年全年有望超过1500亿美元。
“中国企业这一轮对外投资有了更明确的战略目标。当前,中国企业出海投资时,正越来越多地转向新兴市场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长远来看,由于这一轮对外投资的动机更加‘纯粹’,因此后劲也更足。”王庆说。

投资方向更具战略性
在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国内经济承压的大背景下,“出海”已成为不少中国企业寻找新增量的必经之路。
“随着中国国内需求增长放缓及竞争加剧,中国企业正在海外市场寻求增长机会。以往中国企业会考虑进军欧美市场,但鉴于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国企业正转向中东、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其他地区。尽管这些地区的商业及法治环境同样具有挑战性。”锐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贡亚敏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
“国际关系的不可预测性可能导致监管审查和潜在的制裁风险的上升,这使中国公司在海外投资时面临更大的风险”,贡亚敏说,“因此,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对外投资在回暖的同时呈现出更聚焦的战略方向。”
她指出:“当前的投资策略更加侧重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及先进制造、清洁能源、数字经济和自然资源等行业。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也为中国企业在例如东南亚和墨西哥等地投资建厂带来了新机遇。这些投资体现了中国公司对外投资更广泛的一个趋势,即通过多元化产地及利用区域贸易协定来分散风险。”
或面临更严审查
从欧盟《外国补贴条例》(FSR)到美国“长臂管辖”的延伸,新一轮规则博弈下,传统贸易壁垒正快速转变为监管、合规和价值观层面的制度约束。
“并购交易的监管审批风险并不是只有中国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许多跨境并购都有类似的风险。因此,针对这一类风险,国际并购交易市场已经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工具箱’来应对监管审批的不确定性。”王庆说。
他进一步指出:“就外国投资审查而言,审查标准因司法辖区和行业敏感性而异,但中国投资者往往面临更严格的审查,尤其是在美国和印度等国。对于欧盟和英国而言,尽管审查严格,但通常仍可获得批准。企业在设计投资结构时通常可以通过建立当地合作伙伴关系和公司治理安排来降低外界对交易敏感性的认知,并可通过资产剥离、访问限制、供应链安全承诺等补救措施来协助通过审查。”
欧盟FSR的实施尤其值得警惕。“该条例自2023年起生效,已导致部分中国企业放弃项目或面临调查。但只要积极收集证据并加强员工培训,这些挑战是可以应对的”,贡亚敏说。
提前布局
面对种种不确定性和挑战,两位专家也为中企“出海”提供了多项建议:
“要及早与值得信赖的法律顾问合作——选择在全球投资及并购交易方面有成熟经验,并深刻理解目标国法律与监管框架的顾问。”贡亚敏表示,“对于出海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一点尤为关键,因为跨境交易往往涉及中国及东道国复杂且敏感的问题,包括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制裁与出口管制、数据隐私合规等,需予以充分考量与妥善应对,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是敏感的行业。”
王庆表示,“企业还需应对来自多个司法辖区的监管审批流程,并在当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识别并降低交易风险。”
贡亚敏补充指出,“应该在设计投资结构时寻求对投资者最大程度的法律保护,包括利用有利的双边投资协定;开展全面的法律、财务和合规尽职调查,以便在交易早期识别潜在风险和隐患;聚焦合规策略,并在重大交易中纳入应急条款;建立明确的争议解决机制,例如在声誉良好且中立的第三方司法管辖区进行仲裁;制定可行的投资后整合计划,并确保能够实现协同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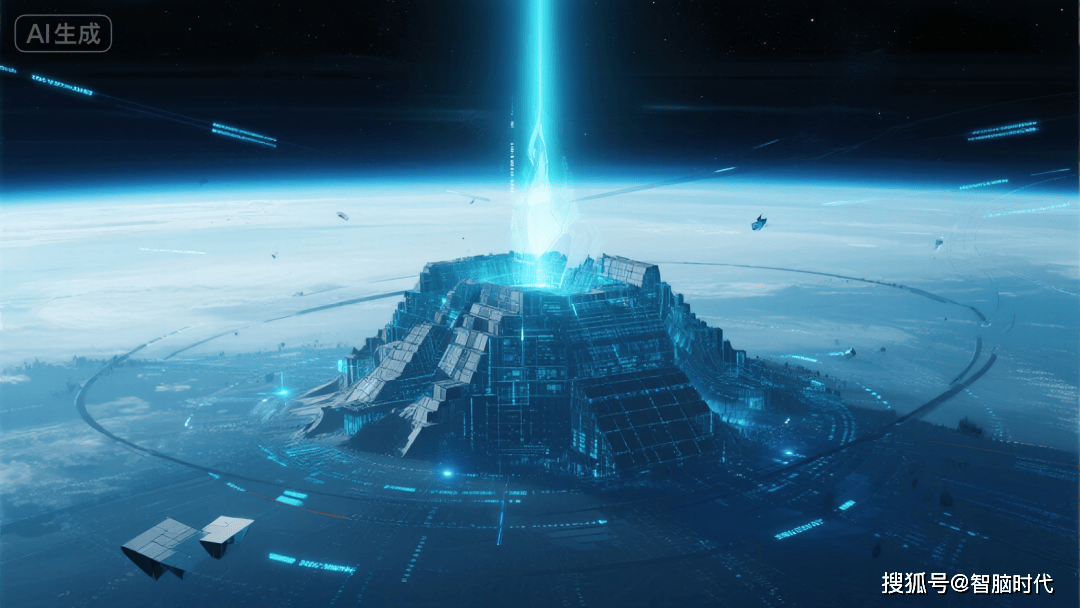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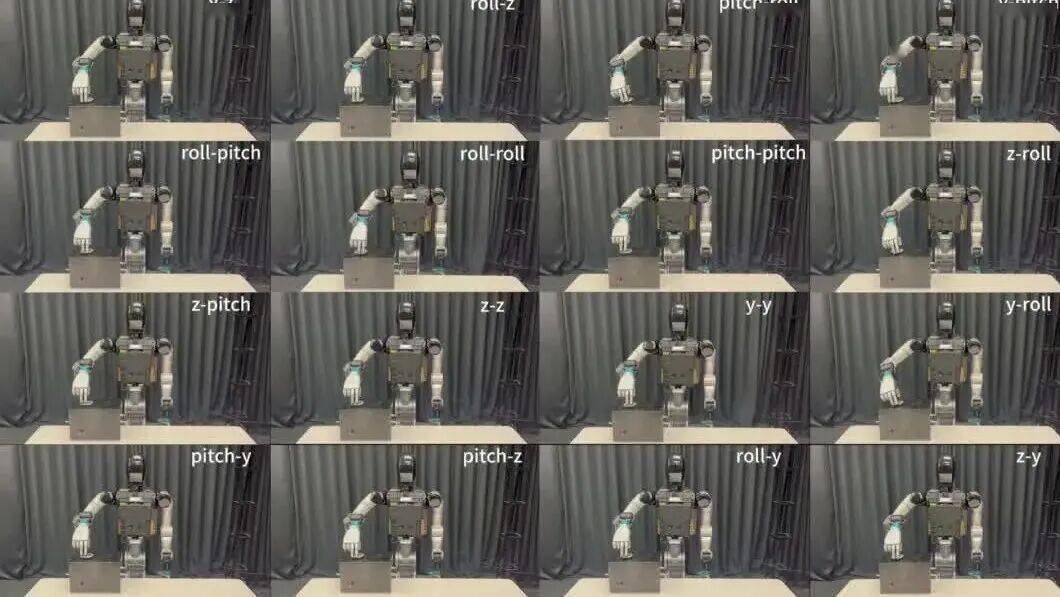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